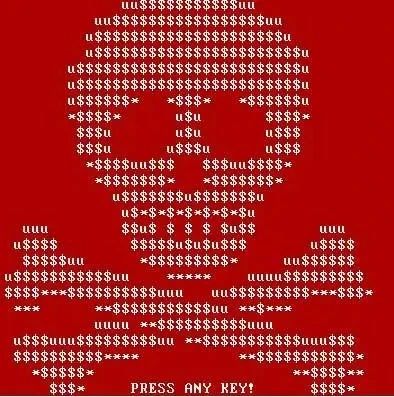□热线电话:(010)64810710□E-mail:artxh@
百家论艺
·2022年3月28日
争鸣
如——王
今八十津京年
需后再看
要话剧《
鞭雾重
策庆谁?》
1940年,中国万岁剧团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宋之的编剧、应云卫导演的《雾重庆》(剧本出版时名为《鞭》),由当时著名话剧演员舒绣文、陈天国、凤子等主演,获得高度赞誉。
1941年,旅港剧人在香港中央大戏院演出该剧,同样引起轰动,之后各地剧团亦纷纷排演。
“雾重庆”更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指称战时重庆复杂的政治局面和经济混乱。
今年3月,重庆市话剧团在北京首都剧场演出该剧,却没能再现当年的辉煌。
虽然演出票销售一空,开场时剧场一楼有八九成上座率,但3个小时后,观众仅剩五成。
第三幕中开始有观众退场,在第三幕、第四幕结束时,走道上更是有人影频繁流动。
究竟是演出不精彩,还是观众没耐心?是时过境迁让这个80年前年轻人的故事失去了审美价值,还是如今的幸福生活蒙蔽了人们的心灵,令我们无法发现这个故事背后的永恒意义?回头细想,这样一场演出或许能带给我们更多思考和启示。
从那本精美的全彩印刷、仿古线装的演出册上,我们能看出与该剧前四版相比,第五版的舞美显然已相当精致。
简陋的阁楼、七七小饭馆、华美的别墅,加上高低错落的山峰,将山城重庆建筑的精致和多样显露无遗。
忧伤凄美的背景音乐和水雾弥漫的舞台效果也在一开场便渲染出愁苦阴郁的基调。
那是1938年,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大量青年学生逃往西南,越来越多的人祈求陪都重庆的庇护。
第一幕中,导演加入了敌机轰炸的背景,第
一,破了“活神仙”万世修“今日敌机不来”的预言;第
二,利用战争的气氛强调了主人公面临的生存压力;第
三,由于关掉了电灯,人物在幽暗的环境中对话,也让人物情绪和舞台色彩有了变化。
真可谓一举三得。
台词方面,删去了林卷妤挑选饭馆家具和餐具时对各色商品的描述,这当然是为了节省时间,但却牺牲了一个展现重庆风土的机会。
二太太被设定为东北人,作为一个性格直爽的人物是合适的,脆生生的东北口音与几个青年学生的普通话形成反差,使舞台语言富有活力。
最出色的设计是导演利用了一个小木马作为沙大千和林卷妤夫妇幼子的象征物。
那显然是那个孩子生前所爱的玩具,现在却只能让年轻的父母睹物伤情,而这个木马在后面竟成为全剧表意的一个核心象征物。
应当说,第一幕的观感是非常舒适的。
七七小饭馆开起来了,红红火火,收入颇丰,但故事却沉闷下去,并且让人开始感到时代的隔膜。
开小饭馆是为了生活,林卷妤更希望能有机会为抗战出力。
老艾第一幕便提醒,不要为了钱忘了工作。
但如 □ 今,他们只能为了生意忙碌,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卷妤的妹妹家棣推荐姐姐参加妇女运动报告会和救护课程,卷妤当然想去,但苦于分身乏术。
此时,早已因家庭困难成为“交际花”的苔莉和官吏袁慕容带来了新的财路。
沙大千决定立刻关闭小饭馆,前往香港做运输生意。
卷妤也就此脱离了厨房之苦。
其实从剧本角度来讲,这一场是众人分道扬镳的重要节点,几个人物的观念冲突也初步显露。
从场面安排的角度讲,这一场是全剧登场人物最多的场次。
忙碌的前堂与后厨,赵肃与顾客的争吵,苔莉和袁慕容的到来,苔莉和老艾的旧怨,家棣对卷妤的告诫,卷妤的愁苦,沙大千的傲慢与得意穿插得错落有致。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据笔者看来,至少有两点,第
一,理想已经改变。
尽管抗战的历史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仍然很重,但毕竟已是过去,如今大学生开饭馆是值得鼓励的创业行为。
这种改变,让原本承担鞭策责任的家棣的告诫显得无力。
当年这出戏是要鞭策青年不要贪图安逸,忘记国家正面临战争,可如今却要鞭策谁呢?当然,我们可以穿越时空,试着去体会人物的心境,但这马上遇到第二个问题,观众对话剧语言审美态度的改变。
第二幕中,苔莉和卷妤都有展现内心痛苦的抒情场面,但那些过于直白激烈的“我心碎了”“我堕落了”之类的台词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品位。
于是,无论从理性角度还是直觉角度,都使得这一场在当年十分精彩的戏难以引起当代观众同样的兴趣。
而当观众兴趣渐消,想要再次吸引其注意力就变得更加困难。
之后,苔莉被袁慕容抛弃,沙大千走上违法道路并被袁慕容陷害,又让林卷妤染上梅毒等,这些情节已在大量社会问题剧和家庭伦理剧中不知被重复了多少次。
而一遍又一遍被吟唱的《嘉陵江上》和幕间的金钱板,除了提醒大家,这是抗战时期的重庆外,也只能营造舒缓的节奏,让观众的神经稍作休息,并不能增加人们对主人公的关心。
于是,开始有观众离场。
在第四幕结束时,林卷妤突然骑上了那个被放大了的木马,我们才赫然感受到一种艺术性的力量。
这个木马,就是第一幕中那个死去的孩子留下的玩具。
而那句“我们是青年”也跟着被点亮。
第五幕中,沙大千再次借木马点出了孩子的意义。
从一开始,那个代表着未来和希望的孩子就死去了,似乎便注定了这些人的堕落。
虽然这一设定体现了创作者为这部旧作寻找新意象的努力,木马的使用也确实起到了相应的效果,但这仍然挽救不了主线情节丧失的现实意义。
其实早在80年前已经有评论指出,这部作品所写的是一种缺陷。
由这缺陷所生的苦闷,由这苦闷所生的侥幸心理,于是主人公们陷进了一个大的混乱。
这个缺陷在当年来说是政治的,更是人们心灵的,是道德良知的缺乏,也是精神意志的脆弱。
我们当然可以联想到,如今这种缺陷仍然存在。
我们要在这一层面上才能找到作品背后的永恒意义。
但现在的问题与当年肯定不同了,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如今只能被当作寓言来看,那些曾经具有典型性的故事和紧迫的社会问题,如今都不足以引起人们的紧张。
80年过去了,话剧的言说方式早已有了更多的选择。
如果我们希望话剧仍然能够起到鞭策的作用,那么创作者们恐怕也需要不断地自我鞭策,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让过去的故事被更多的当代观众所接受。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品味 《寻她芳踪·张爱玲》:多重时空下的“寻找” □谷海慧 日前,在首都剧场的舞台上,由林蔚然与王人凡编剧、李伯男与刘昊导演、浙江话剧团呈现的《寻她芳踪·张爱玲》,是创作者在2020年张爱玲百年诞辰之际,代表“张迷”们对张爱玲进行的一次集体寻找。
受疫情影响,两年后刚刚与北京观众见面。
在这个以“寻找”为关键词的作品中,通过多重时空设计和对张爱玲当下影响的强调,创作者艺术化地完成了“寻找”任务。
戏一开场,舞台上就呈现了三个平行时空:上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1993年的纽约;2020年的杭州。
这三个时空都是物理时空,有极强的现实感,也极具代表性。
它们分别是青年张爱玲横空出世的上海滩、老年张爱玲最后人生阶段的谢幕处、当代“张迷”缅怀张爱玲的聚集地。
从戏份分配上看:重头戏在2020年粉丝们纪念张爱玲百年诞辰活动上,故事的生活实感和当代性也主要借助这一部分实现。
上世纪30、40年代和90年代,上海、纽约两地的篇幅则非常有限。
并且,这两个简写的部分主要通过旁观者叙述完成,即便张爱玲出场,也多与自己青年时代和老年时期的旁观者擦身而过,很少进行对话,从不构成实质性的人物关系。
这种结构设计的奇巧之处在于:一方面突出了张爱玲的当下性,另一方面为艺术创作自由度留下了余地。
实话说,触碰张爱玲这样的人物,如果用传记式手法或取研究式角度,无疑是硬碰硬,即便材料扎实、逻辑缜密、见地新颖,也容易被挑刺。
因为掌故多为共知,秘闻又缺乏信服力,所以不适合传记式方法;而学者的严谨与艺术的浪漫颇难在舞台上兼容,采取研究式角度则往往费力不讨好。
聪明的创作者果断放弃这两种手法,将《寻她芳踪·张爱玲》作为想象、虚构、重组的艺术来经营。
于是,多重时空下的“寻找”开始了。
跟随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和闺蜜炎樱,观众看到了上世纪30、40年代上海滩炙手可热但与时代保持距离的张爱玲;跨越到1993年的纽约,在为见偶像一面而蹲守张爱玲公寓的粉丝小陆带领下,了解了晚年张爱玲寒简的隐居式生活状态;回到 在几组人物情感关系中,《寻她芳踪·张爱玲》创作者找到 了禁闭中的无望、被 伤害的勇敢、真诚付 出与决绝放弃等心理 经验,从而在心理情 感角度为张爱玲画了 像、定了位。
话剧《寻她芳踪·张爱玲》剧照 2020年,民国风情与异域假想都被当下生活取代,贴吧、团建、弹幕、直播、自媒体、网红等时代语素扑面而来,在私人物品展与贴吧活动共同构筑的充满实感与喜感的现实情境下,张爱玲在作品中被当代拥趸解读和演绎。
按说,上述三个物理时空已经提供了寻找张爱玲的多元视角,但创作者更进一步,着眼张爱玲作品,既迈进了张爱玲笔下人物的心理世界,又借此搭建起张爱玲本人的心理时空。
由此形成了一个时空连环套。
在这个时空连环套里,有时,张爱玲是自己与家庭、与上海、与笔下人物关系的冷静陈述者;有时,她与笔下人物合
一,借人物表达自己的人生体认。
参加贴吧活动的四个粉丝,以“戏中戏”形式演绎了《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小团圆》等三部作品片段、朗读了张爱玲经典语录。
三部作品和爱玲语录的选择都极具典型性,非常有助于“寻找” 过程中对张爱玲的理解与贴近。
譬如曼桢被姐姐囚禁时的无助无望,不正是张爱玲被父亲囚禁时的体验?娇蕊对爱的勇敢,又何尝不是张爱玲有过的情感态度?至于九莉与邵之雍从定情到分手的过程,更是被公认充满自传色彩。
创作者选择的这几个女性人物,分别是部分张爱玲的化身。
她们的组合让张爱玲的面貌渐次清晰。
因此,创作者无需让舞台上与现实生活中的张爱玲一一对应,事实上因为历史与现实的隔绝,这种愿望也很难实现;只要选对了张爱玲作品,就能找到她的代言人。
在几组人物情感关系中,《寻她芳踪·张爱玲》创作者找到了禁闭中的无望、被伤害的勇敢、真诚付出与决绝放弃等心理经验,从而在心理情感角度为张爱玲画了像、定了位。
而由粉丝追思会形式进入张爱玲作品,又是如此自然合理、毫不牵强。
舞台上,每个粉丝都既是生活中的自己,又 是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角色张爱玲则与自己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不断进行身份转换,这种设计进一步强化了她和自己笔下女性的同构关系。
尤其重要的是,粉丝追思会的设计还密切了张爱玲与当下的关系。
追思会不仅要求粉丝朗读或演绎张爱玲作品,还规定他们要分享彼此的故事。
而他们自己的故事,无不与张爱玲有关。
粉丝的参与,拉近了张爱玲与当下现实的距离。
张爱玲不是被远观的人,而是与当代阅读者生活息息相关的影响者。
她不仅精准表达了尘世中挣扎的男女的情感,捕捉了他们细密的心思、复杂的情绪,而且长久影响着他们的情感态度、认知与选择。
她不是教科书,不是文学史,她就是进行着的现实。
她既是“此在”,也是“永在”。
因此,上世纪30、40年代、上世纪90年代、新世纪的今天,乃至将来的将来,她仍会被反复阅读、讨论与寻找。
视点 顾长卫电影的摄影风格 □陈云峰 顾长卫于198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从摄影助理开始开启自己的摄影生涯。
他的摄影作品创造性地运用摄影造型手段,大量采用自然光,寻求更加贴近现实表现手段的风格,这样的摄影风格与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的文化命题进行了恰到好处的结合,由其担任摄影的滕文骥执导的电影《海滩》、陈凯歌执导的电影《孩子王》《霸王别姬》和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菊豆》等,无不充满震撼力或某种悠远意境,把中国电影推上世界舞台。
在开始独立创作之后,顾长卫担任导演的电影《立春》《孔雀》《情归同里》《美好2012》《龙头》《最爱》等,也频频让他摘得国内外摄影大奖,展现出其在摄影风格上独到的艺术造诣。
水平镜头中的冷静与克制 在拍摄角度上,顾长卫的影片往往青睐与被摄对象齐平的水平角度,这样的水平镜头配合自然光线的照明形成冷静克制的旁观视角。
冷静克制的拍摄角度所拍摄的画面在角度、光线、色彩、运动、构图上遵从人们的视觉习惯,不追究新奇独特的表现主义风格,被摄物体在标准焦距与适中的摄距中的呈现接近人眼的自然视野。
这种冷静克制的镜头大多是不带有人物主观性的客观镜头,但却仿佛电影人物的旁观者一般一边记录着电影中自然生发的生活之流,一边呈现着现实生活高度浓缩后的艺术世界。
摄影高度影响着画面中人物的感情与态度,顾长卫的电影通常采用镜头与被摄对象高度相等或近似的平角高度,在以人为表现对象的电影中制造出了类似日常生活观察经验相同的视角,同样给人审慎、冷静、克制的印象。
水平的拍摄角度仿佛摄影机对人物的直视,它将一切戏剧化的时间转化为现实范畴中波澜不惊的日常,也把激动的目击者转化为清醒的旁观者。
在《孔雀》中,家中的长女卫红在父母的安排下找到了一份幼儿园保育护工的工作,痴迷乐器的她却因为疏忽造成幼儿摔伤。
卫红的母亲遇事向来果断、凶狠、不择手段,却为了女儿的工作被迫到 摔伤的幼儿家里赔罪。
与人眼等高的水平镜头以冷静旁观的意味,透过幼儿家的窗户见证了这一“屈辱”的过程:起幅画面是幼儿母亲抱着幼儿大声训斥卫红母亲,接着镜头向右平行移动到幼儿的奶奶、爷爷的神态中,他们同样极为傲慢地训斥着卫红母女;镜头继续沿水平方向平移,卫红母亲在打开的窗户玻璃后入画,一向霸道蛮横的她在窗户中恭敬地赔罪,离开前还给这家人鞠了一个躬。
中景画面中,在卫红一家从来说一不
二、象征权力的母亲此时遭遇了更大的“暴力”,即平角度拍摄的摄影机对准一个恰巧从幼儿家中路过的人,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
在一般摄影角度上,傲慢的幼儿家属会出现在比卫红母亲更高的位置上,并以近景拍摄的方式突出争吵的现场感,但顾长卫的镜头却在静观默察中对这样非理性的语言暴力保持了无言,激烈的争吵与冷静审视的态度在克制的水平镜头中形成了默契。
卫红母女自始至终都没有讲话,他们的沉默在平拍角度的镜头下仿佛那个特殊年代人们面对暴力的缩影,更增强了事件的客观性和历史性。
长镜头中的纪实感与生活感 在镜头长度上,顾长卫经常运用长镜头给观众留下纪实主义风格的印象。
在长达数分钟的长镜头中,摄影机以不干预人物行动动作,尽可能还原其生活场景原貌的方式带来了百姓日常的纪实感与生活感。
顾长卫电影中的主角通常是备受生活重担压抑的小人物,而顾长卫保留了电影拍摄者应有的民间立场,以静止不动的画框加强表现画面内物体的运动状态,或对小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历程进行生活化的记录,以一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自然而真实地展现他们在艰难困苦中寻求一线希望的人生。
在顾长卫的电影中,有着大量长镜头使用。
如《立春》,从头到尾都充满着稳健有力的长镜头,尤其在塑造人物性格时,丝毫没有因为情绪表达的迫切便乱了叙事的节奏。
影片以艺校声乐教师王彩玲为主角,这个立志从小县城到北京去发展 的小人物在被生活磨平棱角后选择了独身,开了个肉铺并领养了一个小女孩小凡。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便是王彩玲与养女在天安门广场前戏耍,顾长卫用一个固定长镜头拍摄着放弃所有野心与抱负的王彩玲坐在地上,提示养女小凡背《梅花点点》的儿歌。
顾长卫用这一简单质朴而富有真实感的画面将这一刻的现实感复杂地体现出来:它既是一种洗去铅华的平凡梦想,又是那个年代小人物阶级跃升失败后无可奈何的自我疗愈。
放弃梦想的王彩玲一方面过上了世俗标准中正常的生活,将献身歌剧的艺术理想泯灭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另一方面,她在失去旧有的精神支撑后,养女将作为其新的契机支撑着她在崎岖的生活之途中蹒跚地走下去。
长镜头将影片深刻的寓意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真实、自然,让人信服。
《孔雀》同样以长镜头结尾,这个1分37秒的固定长镜头从动物园的孔雀笼子中朝外拍摄,各自成家立业的儿女们带着他们的孩子走过笼子,而笼子里两只踱步的孔雀始终没有开屏。
在所有人都离去后,其中一只雄孔雀背向镜头突然叫了一声,然后陡然开屏了,在两次缓缓的转身后转向镜头。
此时鲜艳的五彩羽毛在影片压抑的基调下显出惊人的美丽,在客观、真实、自然可信的画面印象中,营造出了源于真实而高于真实的艺术体验。
总之,顾长卫的长镜头为观众呈现出了小人物平凡的日常生活,也以流畅自然的效果在保持了生活原本样貌的同时展示出现实的深层结构,从而创造出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
两极镜头的表现力与戏剧张力 在画面的剪辑与景别选择上,顾长卫对表现同一主体两个大跨度景别的两极镜头格外青睐。
在整体上平实自然的摄影基调中,将近景或特写镜头与远景或全景镜头剪接在一起以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是顾长卫影片中运用得体的表现主义手段。
两极镜头中的“极”指代距离或平面画面中呈现的大小,一边是用全景表现广阔的范围,一边是用特写淋 漓尽致地呈现细节。
两者的拍摄与剪接打破了常规的镜头景别组接顺序,凸显出了镜头组接中的造型意识与摄影机的存在感。
有学者将两级镜头中的景别跳接看作前进式或者后退式运动急拉镜头的变体,在揭示人物内心语言、渲染紧张气氛上、暗示情节走向等方面都有着卓越的表现。
电影《孔雀》中,怀着伞兵梦的卫红躺在楼顶的席子上看跳伞,顾长卫以全景镜头拍摄了她往席子上倒完萝卜条后扔开篮子,伸开双手两脚躺倒在晾萝卜条的席子上,闭上了眼睛;下一个镜头是俯拍特写卫红的面容,她闭着眼一动不动,在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后慢慢睁开眼睛,镜头又切换成了数架飞机从空中掠过的远景画面。
两级镜头从影片当时的社会层面来说,突出了卫红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尽管她只能像随处可见的萝卜条一样晾晒在楼上,但心中却保存着成为飞行员的理想;将这两组镜头剪接在一起,背后隐含的其实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迅速加大,理想的路径难以行通,因此卫红只能在单调乏味的生活中无望地幻想下去。
而在讲述上世纪90年代某偏僻乡村艾滋病患者的影片《最爱》中,两极镜头则成为体现人与人之间差距与隔阂的手段,也在激发影片的戏剧性上有着卓越表现:贫穷的村民们在“血头”赵齐全的诱骗下通过卖血赚钱,但村民乃至其家人都因卖血染上了艾滋病。
患者与普通村民之间又因缺乏对疾病的认识产生了矛盾。
在片头,村民观看盲人拉二胡的情景中,镜头在盲人头部的表情特写、赵齐全父亲老柱柱和赵齐全弟弟赵得意津津有味地观看的表情特写全景画面间来回切换。
在表层叙事中,朴实简单、爱好热闹的村民形象与盲人激情表演的景象在快节奏的二胡音乐中烘托了现场轻松愉快的气氛;但在深层叙事中,这群被赵齐全诱骗,在利益驱使下踏上悲剧之途的村民又是蒙昧的代表。
快节奏的音乐与干净利索的两极镜头营造出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有力地暗示了影片的剧情发展与人物的宿命。
(作者系湖北理工学院师范学院讲师,本文系湖北理工学院2021年“专创融合”课程项目“摄像与音视频编辑”阶段性成果)
1941年,旅港剧人在香港中央大戏院演出该剧,同样引起轰动,之后各地剧团亦纷纷排演。
“雾重庆”更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指称战时重庆复杂的政治局面和经济混乱。
今年3月,重庆市话剧团在北京首都剧场演出该剧,却没能再现当年的辉煌。
虽然演出票销售一空,开场时剧场一楼有八九成上座率,但3个小时后,观众仅剩五成。
第三幕中开始有观众退场,在第三幕、第四幕结束时,走道上更是有人影频繁流动。
究竟是演出不精彩,还是观众没耐心?是时过境迁让这个80年前年轻人的故事失去了审美价值,还是如今的幸福生活蒙蔽了人们的心灵,令我们无法发现这个故事背后的永恒意义?回头细想,这样一场演出或许能带给我们更多思考和启示。
从那本精美的全彩印刷、仿古线装的演出册上,我们能看出与该剧前四版相比,第五版的舞美显然已相当精致。
简陋的阁楼、七七小饭馆、华美的别墅,加上高低错落的山峰,将山城重庆建筑的精致和多样显露无遗。
忧伤凄美的背景音乐和水雾弥漫的舞台效果也在一开场便渲染出愁苦阴郁的基调。
那是1938年,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大量青年学生逃往西南,越来越多的人祈求陪都重庆的庇护。
第一幕中,导演加入了敌机轰炸的背景,第
一,破了“活神仙”万世修“今日敌机不来”的预言;第
二,利用战争的气氛强调了主人公面临的生存压力;第
三,由于关掉了电灯,人物在幽暗的环境中对话,也让人物情绪和舞台色彩有了变化。
真可谓一举三得。
台词方面,删去了林卷妤挑选饭馆家具和餐具时对各色商品的描述,这当然是为了节省时间,但却牺牲了一个展现重庆风土的机会。
二太太被设定为东北人,作为一个性格直爽的人物是合适的,脆生生的东北口音与几个青年学生的普通话形成反差,使舞台语言富有活力。
最出色的设计是导演利用了一个小木马作为沙大千和林卷妤夫妇幼子的象征物。
那显然是那个孩子生前所爱的玩具,现在却只能让年轻的父母睹物伤情,而这个木马在后面竟成为全剧表意的一个核心象征物。
应当说,第一幕的观感是非常舒适的。
七七小饭馆开起来了,红红火火,收入颇丰,但故事却沉闷下去,并且让人开始感到时代的隔膜。
开小饭馆是为了生活,林卷妤更希望能有机会为抗战出力。
老艾第一幕便提醒,不要为了钱忘了工作。
但如 □ 今,他们只能为了生意忙碌,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卷妤的妹妹家棣推荐姐姐参加妇女运动报告会和救护课程,卷妤当然想去,但苦于分身乏术。
此时,早已因家庭困难成为“交际花”的苔莉和官吏袁慕容带来了新的财路。
沙大千决定立刻关闭小饭馆,前往香港做运输生意。
卷妤也就此脱离了厨房之苦。
其实从剧本角度来讲,这一场是众人分道扬镳的重要节点,几个人物的观念冲突也初步显露。
从场面安排的角度讲,这一场是全剧登场人物最多的场次。
忙碌的前堂与后厨,赵肃与顾客的争吵,苔莉和袁慕容的到来,苔莉和老艾的旧怨,家棣对卷妤的告诫,卷妤的愁苦,沙大千的傲慢与得意穿插得错落有致。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据笔者看来,至少有两点,第
一,理想已经改变。
尽管抗战的历史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仍然很重,但毕竟已是过去,如今大学生开饭馆是值得鼓励的创业行为。
这种改变,让原本承担鞭策责任的家棣的告诫显得无力。
当年这出戏是要鞭策青年不要贪图安逸,忘记国家正面临战争,可如今却要鞭策谁呢?当然,我们可以穿越时空,试着去体会人物的心境,但这马上遇到第二个问题,观众对话剧语言审美态度的改变。
第二幕中,苔莉和卷妤都有展现内心痛苦的抒情场面,但那些过于直白激烈的“我心碎了”“我堕落了”之类的台词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品位。
于是,无论从理性角度还是直觉角度,都使得这一场在当年十分精彩的戏难以引起当代观众同样的兴趣。
而当观众兴趣渐消,想要再次吸引其注意力就变得更加困难。
之后,苔莉被袁慕容抛弃,沙大千走上违法道路并被袁慕容陷害,又让林卷妤染上梅毒等,这些情节已在大量社会问题剧和家庭伦理剧中不知被重复了多少次。
而一遍又一遍被吟唱的《嘉陵江上》和幕间的金钱板,除了提醒大家,这是抗战时期的重庆外,也只能营造舒缓的节奏,让观众的神经稍作休息,并不能增加人们对主人公的关心。
于是,开始有观众离场。
在第四幕结束时,林卷妤突然骑上了那个被放大了的木马,我们才赫然感受到一种艺术性的力量。
这个木马,就是第一幕中那个死去的孩子留下的玩具。
而那句“我们是青年”也跟着被点亮。
第五幕中,沙大千再次借木马点出了孩子的意义。
从一开始,那个代表着未来和希望的孩子就死去了,似乎便注定了这些人的堕落。
虽然这一设定体现了创作者为这部旧作寻找新意象的努力,木马的使用也确实起到了相应的效果,但这仍然挽救不了主线情节丧失的现实意义。
其实早在80年前已经有评论指出,这部作品所写的是一种缺陷。
由这缺陷所生的苦闷,由这苦闷所生的侥幸心理,于是主人公们陷进了一个大的混乱。
这个缺陷在当年来说是政治的,更是人们心灵的,是道德良知的缺乏,也是精神意志的脆弱。
我们当然可以联想到,如今这种缺陷仍然存在。
我们要在这一层面上才能找到作品背后的永恒意义。
但现在的问题与当年肯定不同了,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如今只能被当作寓言来看,那些曾经具有典型性的故事和紧迫的社会问题,如今都不足以引起人们的紧张。
80年过去了,话剧的言说方式早已有了更多的选择。
如果我们希望话剧仍然能够起到鞭策的作用,那么创作者们恐怕也需要不断地自我鞭策,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让过去的故事被更多的当代观众所接受。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品味 《寻她芳踪·张爱玲》:多重时空下的“寻找” □谷海慧 日前,在首都剧场的舞台上,由林蔚然与王人凡编剧、李伯男与刘昊导演、浙江话剧团呈现的《寻她芳踪·张爱玲》,是创作者在2020年张爱玲百年诞辰之际,代表“张迷”们对张爱玲进行的一次集体寻找。
受疫情影响,两年后刚刚与北京观众见面。
在这个以“寻找”为关键词的作品中,通过多重时空设计和对张爱玲当下影响的强调,创作者艺术化地完成了“寻找”任务。
戏一开场,舞台上就呈现了三个平行时空:上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1993年的纽约;2020年的杭州。
这三个时空都是物理时空,有极强的现实感,也极具代表性。
它们分别是青年张爱玲横空出世的上海滩、老年张爱玲最后人生阶段的谢幕处、当代“张迷”缅怀张爱玲的聚集地。
从戏份分配上看:重头戏在2020年粉丝们纪念张爱玲百年诞辰活动上,故事的生活实感和当代性也主要借助这一部分实现。
上世纪30、40年代和90年代,上海、纽约两地的篇幅则非常有限。
并且,这两个简写的部分主要通过旁观者叙述完成,即便张爱玲出场,也多与自己青年时代和老年时期的旁观者擦身而过,很少进行对话,从不构成实质性的人物关系。
这种结构设计的奇巧之处在于:一方面突出了张爱玲的当下性,另一方面为艺术创作自由度留下了余地。
实话说,触碰张爱玲这样的人物,如果用传记式手法或取研究式角度,无疑是硬碰硬,即便材料扎实、逻辑缜密、见地新颖,也容易被挑刺。
因为掌故多为共知,秘闻又缺乏信服力,所以不适合传记式方法;而学者的严谨与艺术的浪漫颇难在舞台上兼容,采取研究式角度则往往费力不讨好。
聪明的创作者果断放弃这两种手法,将《寻她芳踪·张爱玲》作为想象、虚构、重组的艺术来经营。
于是,多重时空下的“寻找”开始了。
跟随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和闺蜜炎樱,观众看到了上世纪30、40年代上海滩炙手可热但与时代保持距离的张爱玲;跨越到1993年的纽约,在为见偶像一面而蹲守张爱玲公寓的粉丝小陆带领下,了解了晚年张爱玲寒简的隐居式生活状态;回到 在几组人物情感关系中,《寻她芳踪·张爱玲》创作者找到 了禁闭中的无望、被 伤害的勇敢、真诚付 出与决绝放弃等心理 经验,从而在心理情 感角度为张爱玲画了 像、定了位。
话剧《寻她芳踪·张爱玲》剧照 2020年,民国风情与异域假想都被当下生活取代,贴吧、团建、弹幕、直播、自媒体、网红等时代语素扑面而来,在私人物品展与贴吧活动共同构筑的充满实感与喜感的现实情境下,张爱玲在作品中被当代拥趸解读和演绎。
按说,上述三个物理时空已经提供了寻找张爱玲的多元视角,但创作者更进一步,着眼张爱玲作品,既迈进了张爱玲笔下人物的心理世界,又借此搭建起张爱玲本人的心理时空。
由此形成了一个时空连环套。
在这个时空连环套里,有时,张爱玲是自己与家庭、与上海、与笔下人物关系的冷静陈述者;有时,她与笔下人物合
一,借人物表达自己的人生体认。
参加贴吧活动的四个粉丝,以“戏中戏”形式演绎了《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小团圆》等三部作品片段、朗读了张爱玲经典语录。
三部作品和爱玲语录的选择都极具典型性,非常有助于“寻找” 过程中对张爱玲的理解与贴近。
譬如曼桢被姐姐囚禁时的无助无望,不正是张爱玲被父亲囚禁时的体验?娇蕊对爱的勇敢,又何尝不是张爱玲有过的情感态度?至于九莉与邵之雍从定情到分手的过程,更是被公认充满自传色彩。
创作者选择的这几个女性人物,分别是部分张爱玲的化身。
她们的组合让张爱玲的面貌渐次清晰。
因此,创作者无需让舞台上与现实生活中的张爱玲一一对应,事实上因为历史与现实的隔绝,这种愿望也很难实现;只要选对了张爱玲作品,就能找到她的代言人。
在几组人物情感关系中,《寻她芳踪·张爱玲》创作者找到了禁闭中的无望、被伤害的勇敢、真诚付出与决绝放弃等心理经验,从而在心理情感角度为张爱玲画了像、定了位。
而由粉丝追思会形式进入张爱玲作品,又是如此自然合理、毫不牵强。
舞台上,每个粉丝都既是生活中的自己,又 是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角色张爱玲则与自己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不断进行身份转换,这种设计进一步强化了她和自己笔下女性的同构关系。
尤其重要的是,粉丝追思会的设计还密切了张爱玲与当下的关系。
追思会不仅要求粉丝朗读或演绎张爱玲作品,还规定他们要分享彼此的故事。
而他们自己的故事,无不与张爱玲有关。
粉丝的参与,拉近了张爱玲与当下现实的距离。
张爱玲不是被远观的人,而是与当代阅读者生活息息相关的影响者。
她不仅精准表达了尘世中挣扎的男女的情感,捕捉了他们细密的心思、复杂的情绪,而且长久影响着他们的情感态度、认知与选择。
她不是教科书,不是文学史,她就是进行着的现实。
她既是“此在”,也是“永在”。
因此,上世纪30、40年代、上世纪90年代、新世纪的今天,乃至将来的将来,她仍会被反复阅读、讨论与寻找。
视点 顾长卫电影的摄影风格 □陈云峰 顾长卫于198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从摄影助理开始开启自己的摄影生涯。
他的摄影作品创造性地运用摄影造型手段,大量采用自然光,寻求更加贴近现实表现手段的风格,这样的摄影风格与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的文化命题进行了恰到好处的结合,由其担任摄影的滕文骥执导的电影《海滩》、陈凯歌执导的电影《孩子王》《霸王别姬》和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菊豆》等,无不充满震撼力或某种悠远意境,把中国电影推上世界舞台。
在开始独立创作之后,顾长卫担任导演的电影《立春》《孔雀》《情归同里》《美好2012》《龙头》《最爱》等,也频频让他摘得国内外摄影大奖,展现出其在摄影风格上独到的艺术造诣。
水平镜头中的冷静与克制 在拍摄角度上,顾长卫的影片往往青睐与被摄对象齐平的水平角度,这样的水平镜头配合自然光线的照明形成冷静克制的旁观视角。
冷静克制的拍摄角度所拍摄的画面在角度、光线、色彩、运动、构图上遵从人们的视觉习惯,不追究新奇独特的表现主义风格,被摄物体在标准焦距与适中的摄距中的呈现接近人眼的自然视野。
这种冷静克制的镜头大多是不带有人物主观性的客观镜头,但却仿佛电影人物的旁观者一般一边记录着电影中自然生发的生活之流,一边呈现着现实生活高度浓缩后的艺术世界。
摄影高度影响着画面中人物的感情与态度,顾长卫的电影通常采用镜头与被摄对象高度相等或近似的平角高度,在以人为表现对象的电影中制造出了类似日常生活观察经验相同的视角,同样给人审慎、冷静、克制的印象。
水平的拍摄角度仿佛摄影机对人物的直视,它将一切戏剧化的时间转化为现实范畴中波澜不惊的日常,也把激动的目击者转化为清醒的旁观者。
在《孔雀》中,家中的长女卫红在父母的安排下找到了一份幼儿园保育护工的工作,痴迷乐器的她却因为疏忽造成幼儿摔伤。
卫红的母亲遇事向来果断、凶狠、不择手段,却为了女儿的工作被迫到 摔伤的幼儿家里赔罪。
与人眼等高的水平镜头以冷静旁观的意味,透过幼儿家的窗户见证了这一“屈辱”的过程:起幅画面是幼儿母亲抱着幼儿大声训斥卫红母亲,接着镜头向右平行移动到幼儿的奶奶、爷爷的神态中,他们同样极为傲慢地训斥着卫红母女;镜头继续沿水平方向平移,卫红母亲在打开的窗户玻璃后入画,一向霸道蛮横的她在窗户中恭敬地赔罪,离开前还给这家人鞠了一个躬。
中景画面中,在卫红一家从来说一不
二、象征权力的母亲此时遭遇了更大的“暴力”,即平角度拍摄的摄影机对准一个恰巧从幼儿家中路过的人,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
在一般摄影角度上,傲慢的幼儿家属会出现在比卫红母亲更高的位置上,并以近景拍摄的方式突出争吵的现场感,但顾长卫的镜头却在静观默察中对这样非理性的语言暴力保持了无言,激烈的争吵与冷静审视的态度在克制的水平镜头中形成了默契。
卫红母女自始至终都没有讲话,他们的沉默在平拍角度的镜头下仿佛那个特殊年代人们面对暴力的缩影,更增强了事件的客观性和历史性。
长镜头中的纪实感与生活感 在镜头长度上,顾长卫经常运用长镜头给观众留下纪实主义风格的印象。
在长达数分钟的长镜头中,摄影机以不干预人物行动动作,尽可能还原其生活场景原貌的方式带来了百姓日常的纪实感与生活感。
顾长卫电影中的主角通常是备受生活重担压抑的小人物,而顾长卫保留了电影拍摄者应有的民间立场,以静止不动的画框加强表现画面内物体的运动状态,或对小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历程进行生活化的记录,以一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自然而真实地展现他们在艰难困苦中寻求一线希望的人生。
在顾长卫的电影中,有着大量长镜头使用。
如《立春》,从头到尾都充满着稳健有力的长镜头,尤其在塑造人物性格时,丝毫没有因为情绪表达的迫切便乱了叙事的节奏。
影片以艺校声乐教师王彩玲为主角,这个立志从小县城到北京去发展 的小人物在被生活磨平棱角后选择了独身,开了个肉铺并领养了一个小女孩小凡。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便是王彩玲与养女在天安门广场前戏耍,顾长卫用一个固定长镜头拍摄着放弃所有野心与抱负的王彩玲坐在地上,提示养女小凡背《梅花点点》的儿歌。
顾长卫用这一简单质朴而富有真实感的画面将这一刻的现实感复杂地体现出来:它既是一种洗去铅华的平凡梦想,又是那个年代小人物阶级跃升失败后无可奈何的自我疗愈。
放弃梦想的王彩玲一方面过上了世俗标准中正常的生活,将献身歌剧的艺术理想泯灭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另一方面,她在失去旧有的精神支撑后,养女将作为其新的契机支撑着她在崎岖的生活之途中蹒跚地走下去。
长镜头将影片深刻的寓意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真实、自然,让人信服。
《孔雀》同样以长镜头结尾,这个1分37秒的固定长镜头从动物园的孔雀笼子中朝外拍摄,各自成家立业的儿女们带着他们的孩子走过笼子,而笼子里两只踱步的孔雀始终没有开屏。
在所有人都离去后,其中一只雄孔雀背向镜头突然叫了一声,然后陡然开屏了,在两次缓缓的转身后转向镜头。
此时鲜艳的五彩羽毛在影片压抑的基调下显出惊人的美丽,在客观、真实、自然可信的画面印象中,营造出了源于真实而高于真实的艺术体验。
总之,顾长卫的长镜头为观众呈现出了小人物平凡的日常生活,也以流畅自然的效果在保持了生活原本样貌的同时展示出现实的深层结构,从而创造出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
两极镜头的表现力与戏剧张力 在画面的剪辑与景别选择上,顾长卫对表现同一主体两个大跨度景别的两极镜头格外青睐。
在整体上平实自然的摄影基调中,将近景或特写镜头与远景或全景镜头剪接在一起以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是顾长卫影片中运用得体的表现主义手段。
两极镜头中的“极”指代距离或平面画面中呈现的大小,一边是用全景表现广阔的范围,一边是用特写淋 漓尽致地呈现细节。
两者的拍摄与剪接打破了常规的镜头景别组接顺序,凸显出了镜头组接中的造型意识与摄影机的存在感。
有学者将两级镜头中的景别跳接看作前进式或者后退式运动急拉镜头的变体,在揭示人物内心语言、渲染紧张气氛上、暗示情节走向等方面都有着卓越的表现。
电影《孔雀》中,怀着伞兵梦的卫红躺在楼顶的席子上看跳伞,顾长卫以全景镜头拍摄了她往席子上倒完萝卜条后扔开篮子,伸开双手两脚躺倒在晾萝卜条的席子上,闭上了眼睛;下一个镜头是俯拍特写卫红的面容,她闭着眼一动不动,在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后慢慢睁开眼睛,镜头又切换成了数架飞机从空中掠过的远景画面。
两级镜头从影片当时的社会层面来说,突出了卫红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尽管她只能像随处可见的萝卜条一样晾晒在楼上,但心中却保存着成为飞行员的理想;将这两组镜头剪接在一起,背后隐含的其实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迅速加大,理想的路径难以行通,因此卫红只能在单调乏味的生活中无望地幻想下去。
而在讲述上世纪90年代某偏僻乡村艾滋病患者的影片《最爱》中,两极镜头则成为体现人与人之间差距与隔阂的手段,也在激发影片的戏剧性上有着卓越表现:贫穷的村民们在“血头”赵齐全的诱骗下通过卖血赚钱,但村民乃至其家人都因卖血染上了艾滋病。
患者与普通村民之间又因缺乏对疾病的认识产生了矛盾。
在片头,村民观看盲人拉二胡的情景中,镜头在盲人头部的表情特写、赵齐全父亲老柱柱和赵齐全弟弟赵得意津津有味地观看的表情特写全景画面间来回切换。
在表层叙事中,朴实简单、爱好热闹的村民形象与盲人激情表演的景象在快节奏的二胡音乐中烘托了现场轻松愉快的气氛;但在深层叙事中,这群被赵齐全诱骗,在利益驱使下踏上悲剧之途的村民又是蒙昧的代表。
快节奏的音乐与干净利索的两极镜头营造出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有力地暗示了影片的剧情发展与人物的宿命。
(作者系湖北理工学院师范学院讲师,本文系湖北理工学院2021年“专创融合”课程项目“摄像与音视频编辑”阶段性成果)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