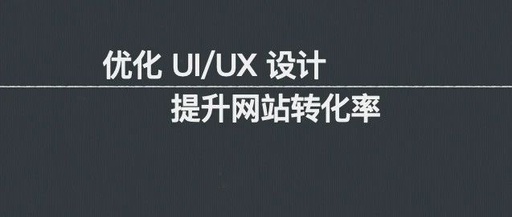责任编辑:张楚藩电话:2356773传真:2265261投稿网址:/contribute.asp
2009年5月19日星期
二 http押//www.chaozhoudaily.com 温暖的手掌 □程毅飞 每当看电视看到父母不辞辛劳教养子女的镜头时,我就忍不住会想起父亲那温暖的手掌。
小时候,从我记事时起,家里的日子一直就很清苦。
虽然父亲是赤脚医生,收入比别的人家稍好一些,但生产队分的那点口粮还是不够吃,父亲总是在诊完病后,东坡跑到西坡地寻野菜,拿回家让母亲掺上一点点面粉蒸熟让我们吃。
我让父母跟我们一块吃,他们总是摆摆手说:“我们已经吃过了......”可我从父母那困乏无力的神态中知道他们是在哄骗我们。
一次放学回家,村头摆放着一个外乡人进村卖东西的挑担,见四下无人,我就随手拿了一根麻花,跑回家想给父母吃。
父亲问我:“麻花是从哪儿弄的?”我说:“别人给的。
”父亲不信,说:“你小小年纪就学会撒谎了。
今儿你要是不说实话,爹就不吃你给的麻花。
”我想让父亲吃了那麻花,就实话告诉了他。
谁知,当他听到麻花是从别人那里偷来时,一把拽住我的衣领,狠狠给了我一个耳光,又把我带到卖麻花人跟前,一边让我把麻花还回去,一边向那人道歉:“是我家孩子拿了你的麻花,小孩子不懂事,都怪我平日没管教好!”看到父亲低声下气的样子,我悔恨极了。
回到家中,父亲的气还没有消尽,在我的屁股上又抽了几个巴掌,然后罚我跪在场院边的核桃树下。
他在院旁一边沤着猪粪,一边发出阵阵叹息声。
看到父亲伤心的样子,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哽咽着说:“爹......我错了,以后......”父亲放下手中的铁耙,用他那宽厚的手掌捧着我的脸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呀,你要永远记着,咱人穷,可志不能短啊!”我扑在父亲怀里哭了起来,一向刚强的父亲一边用他粗糙的手掌给我擦眼泪,一边抱着我也哭了。
后来,土地承包到户,吃的不愁了,父亲多年紧锁的眉头也舒展了。
为方便村民就医,他在村口办起了医疗站,规模虽小,但药品还算齐全。
对来买药的村民,他都是按药品的进价售出,从不赚乡亲们一分钱。
村里的孤寡老人和家庭困难户有个头疼脑热,他都会主动带上药物上门给他们诊治,从来不提钱不钱的,有的人家给钱让急了,父亲最多只收一半的药费。
为此母亲还跟父亲吵过几次嘴,我也在父亲面前表示过不满。
父亲也不发火,拍拍我的脸蛋说:“孩子,与人为善,这是做人的本分,你爹能当上村赤脚医生,就是大家在抬举咱们,你说爹不为他们着想为谁着想?”我觉得父亲的巴掌轻轻的、暖暖的。
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父亲别提有多高兴了,整天进进出出脸上都挂着笑,他说要让村里的乡亲来家聚一聚,既是感谢大家,也是向我表示祝贺。
可谁曾想,事情还没有开始操办,小妹却得了病,父亲和大哥只好带着小妹去省城的大医院治疗。
临出门,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儿呀,爹对不住你,等以后有时间再给你补上,我和你大哥这一走可能得十天半月的,家里就交给你了。
”说完,他就走出了家门,我看到父亲眼 里有泪花在闪,隐隐觉出小妹的病可能不轻。
快入学的时候,父亲一个人回来了,仅仅半个月时间,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整个人似乎也老了许多。
我问小妹的病怎么样,他只是说没什么大碍,让我不要操心,只管上学就是。
那一夜,我闹肚子经过父母的窗下,听到他们谈话,才知道小妹得的是胃癌,已经是晚期,在省城住院花光了家里的钱,父亲这次回家一是借住院费,二是想办法让我尽快去上学。
他们不想让我知道实情。
我听到父亲在不停地叹息,母亲也在低声地哭泣着。
第二天,我醒来没见着父亲,只看到母亲的眼泡肿涨得很高,问她,她说父亲天不亮就出了门。
我知道他是去借钱了。
快到吃饭的时辰,父亲回来了。
我走上去对他说:“爹,我不想上大学了,我想出去挣钱。
”听了我的话,父亲额头的青筋一根根暴了起来,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对我吼道:“你说啥?你再给我说一遍!”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见到父亲那样发过凶,就躲进里屋大声哭了起来,母亲也陪着我流眼泪。
看到这情形,父亲走过来心平气和地说:“有难处有啥怕,想想办法能挺过去的,不是还有乡亲邻里们帮忙吗!”说着,他就把一个纸包交到了母亲手中。
两天后,我踏上了上学的路,父亲送我到县城,又把我送上了去远方的客车。
临别时,他把一个装有2000元钱的牛皮纸袋交给我,说:“到了学校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一片心意。
饭一定要吃饱,正在长身体,不要搞坏了身子。
钱不够了就给家里写信,爹给你寄......”他一边说着,手不停地抚着我的脸。
车要开了,他却抓着我的双手久久不愿放开。
小妹终于没能留住,她还是走了,那年她才刚刚16岁。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父亲送我去县城的时候,小妹已经不行了,父亲是知道的,可他瞒着我。
这时我才明了,父亲那天为什么久久抓着我的手不愿放开。
坚强的父亲是怎样忍着内心的悲痛目送我离去的呀……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县城工作。
我加倍努力,想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可是,天不遂人愿,不久父亲就查出患有与小妹同样的病,而且也是到了晚期。
我和大哥要送他去省城治疗,可他说什么也不肯,我们逼急了,他就说:“我知道我得的是啥病,没用的,不要瞎糟蹋钱了,害得你们以后背一身的债,那样,就是我死了也不会闭上眼睛的。
”无奈,只得用药物保守治疗。
油尽灯灭。
父亲终究没能挨过那个寒冷的冬天,在腊月初一离我们而去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父亲把我们叫到身边,看着我们一句话也不说,用手不停地抚摸着我和大哥的头。
我依在父亲身边,紧紧攥住他瘦如干柴的双手,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泪水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
如今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对父亲的思念却愈加强烈。
每每想起,总有一双宽厚的巴掌在我心里抚来摸去,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温暖。
父亲与草鞋 □莫文勇 父亲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一生爱穿草鞋。
记得十三岁那年冬天,我看见父亲的脚被冻得皲裂流血,仍然穿草鞋。
我不解地问“:天这么冷,您怎么还穿草鞋?”父亲动了动嘴唇,欲言又止。
晚上,父亲拿出一件东西,是用牛皮纸包着的。
他神情严肃,慢慢拆开了牛皮纸包,里面的东西还用红布包裹着。
在我们乡间,只有很珍贵的东西才用红布包起来珍藏。
我心想:这究竟是什么宝物呢?红布打开了,竟是一双将要穿烂的草鞋,因年久,已经变色,还带有点霉味。
我惊讶地问父亲“:您怎么把一双旧草鞋这样藏起来?”见我疑惑,父亲慢慢讲述了他与草鞋的情缘。
解放前夕,父亲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被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
他不愿为旧军队卖命,没过几天便在一个夜晚逃了出来。
怕被抓回去,他只得扔掉一身军装,光着脚在荆棘丛生的大山上朝着家乡的方向逃跑。
脚腿不时被刺伤、划破,痛苦不堪。
走着走着,不知到了悬崖边,父亲一脚步踩下去,一根尖利的木桩刺进了脚心,钻心透骨般疼痛。
他一收脚,便一个踉跄跌下悬崖,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日头偏西。
他满身是伤,脑壳发晕,又饥又渴,无力动弹了。
在那荒山密林中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想到远在家乡的父母,禁不住伤心落泪。
正在父亲绝望之时,来了一对上山捡柴的农家婆媳。
见了我父亲,问明缘由后,把我父亲背回她家医治养伤,直到伤愈。
临别时,大娘拿出一双崭新的草鞋,对父亲说:“穿上,免得又伤了脚……”父亲穿着新草鞋,循着老大娘指的路,终于逃回了家。
一回到家,他就把这双草鞋珍藏起来。
我恍然大悟,终于第一次“读”懂了父亲脚上草鞋的价值。
我上高中时,母亲早已去世。
父亲年逾花甲,又当爹又当妈,日夜操劳供我读书。
一个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我们学生关着教室的门窗读书。
第一节下课时,我刚走出教室就看见父亲走来。
他脚上穿着一双崭新草鞋,双脚冻得发红,还裂开大大小小的口子,流着血丝。
我鼻子一酸,心里一阵难过。
父亲却笑了笑先开口:“天气这么冷,我想你没有菜钱了,给你送来两块钱,又带两件旧衣服来,好加在身上。
”老家离学校五十多里,父亲竟来得这么早,我问:“坐车来的?”父亲说:“天未亮就动身来学校。
”我心里一酸,泪水盈满了眼眶。
我从父亲手中缓缓接过那还带着父亲体温的两元钱,感到异常沉重。
“好好读书吧,我走了。
”父亲说完,转身就走了。
望着穿着草鞋的父亲远去的背影,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山路弯弯 □路边青草 小余是我的一位小学同学,他家在一个叫下坝溪的地方,那是离我的村子有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山中小村。
前些天假日,我们都从外面回老家,小余约我一块去他的山里老家下坝溪玩,因为眼下正是他们老家山上杨梅熟的时节,我们上山摘杨梅去!去下坝溪摘杨梅回来,碰到村子里的曾奶奶,那是一位八十岁的老阿婆。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了,她遇到我自是很亲切,问了很多话,我说我去下坝溪摘杨梅回来呢。
我又问:“曾奶奶,你去过下坝溪吗?” “去过,但离现在都四十多年了。
我去得少,老义去得多,同行的经常都有十多人,那都是我们村里的青壮男子。
” 曾奶奶说的老义,是她的老公,不过已经去世多年了。
“大家去那里做什么呢?”“那时大家都过得辛苦啊,去下坝溪找饭吃,就是———挑担。
”“挑担?”“就是帮人挑东西,天天挑一担东西,往返于我们村里与下坝溪之间。
”“挑什么东西呢?”“挑石灰。
”于是,曾奶奶与我聊起了当年的事情。
人要生活,总得有居所,要建房屋,就少不了原材料。
下坝溪是山村,所需要的建筑材料,都是从山外买进去的,那时的交通和运输都落后,汽车根本是没有的,即使有 车,山路太小也是行走不了,所需的水泥砖瓦石头石灰,完全是靠人工一担一担挑运,而大家把给别人挑运东西,叫做“挑担”。
其实不仅仅是下坝溪,很多山里山外的大小村子建造房屋,所需的材料都是靠人挑运的。
老义是我们村里挑担的领头,因为那时大家都要去生产队集体劳动干活,只有闲余的时候,才能偶尔去挑一下担赚点外快。
但老义不去生产队干活,专职的“搞副业”,因为没有去生产队劳动,所以每个月要向生产队交36块钱的“副业款”。
下坝溪离得远,来回50公里路。
人的走路速度一个小时是一铺路(5公里)左右,十铺路,得走上十个小时。
即使空手连续走上十个小时的路,人也是会累、并且越走越慢的,何况身上还要挑一百斤重的东西呢!半路上歇息和耽搁的时间,自是不少的了,到了目的地,和买主又少不了交谈和喝水的时间。
所以,这十铺挑担路,真是“出门黑天,回家天黑”。
在黑夜中行走的路程也很长。
山间的晚上可不像城市里的晚上,山间要是没有星星和月亮的话,则是完全彻底地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挑担的人,便要举着火把照明。
照明的火把,可不是点的汽油煤油,而是竹子。
去山上砍来一种小竹子,把它们砸扁,在水池里浸泡上半个月,再捞起晒干后,易燃也耐燃。
挑担时通常都有伙伴,所以挑担的人,每个人除了挑上百斤的石灰 重担,和路上吃喝的干粮茶水外,每个人同时也都还得携带上几斤的干竹子以供照明,你的点完了就点他的,他的烧完了,就点另一个人的。
如果竹子没有烧完的话,则扔在路上,晚上回家的时候,又可捡来点着照明用。
曾奶奶那时才30多岁,还很年轻,每天也去生产队干活,有空的时候,头天便去镇上石灰厂买回一担石灰挑回来,算是减轻一下老义的工作量,老义第二天便把这担石灰挑到下坝溪去。
曾奶奶没有空的时候,则要老义自己去石灰厂买,镇上的石灰厂离村子也有五六公里路,需要老义自己去购买石灰的时候,这又得花去很多准备时间,则当天是不可能去下坝溪的了,得等到第二天再挑出门。
所以一个月下来,即使你是铁人,通常只能往返15担左右,最多的时候,也只是20担。
石灰挑到了下坝溪,买来是6角钱一百斤,卖价是3元钱,也就是一百斤有2元4角钱的利润。
一个月如果挑了15担一百斤的,一担赚2元4角,则赚到36元,刚好够交给生产队作副业款,自己就一分钱也不剩了。
一个月如果挑到20担,则可赚到48元,减掉交给生产队的,一个月下来能赚到12元钱。
很多人其实挑不到一百斤的石灰,只能挑到七八十斤,但加上扁担竹篓、竹子火把、干粮茶水,总重量也是上百斤了。
为了多挣钱,老义的挑担重量,经常都有一百三四十斤。
老义赚到的钱,通常一个月就是10块钱左右。
10块钱,可以买几十斤的粮食和应付一些油盐柴火等开支了,但这可是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啊!老二养了五个小孩子,还有父母,一家人吃的饭量可说是很不小的。
那时的大米价格,国家卖的是1角4分钱一斤,因为粮食紧缺,去买黑市的大米的话,价格则要6角钱一斤。
所以老义接的活计,一天也断不得,因为接的活计一断,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不能向生产队交钱,也不能维持自己家里吃用开支了。
其实,他做熟了,活是长年都不缺的,这里的活计接完,马上有下一个活接。
因为建房子所需的材料,毕竟不是一担两担能解决的,一个人挑一担往返时间需要一天,一个月下来也只能挑到十几担,对建房子来说远远不够,所以接到一个活,一个人还经常忙不过来,老义便经常叫上村里的人一块去挑担“赚钱”。
除了“赚钱”,有时也“赚物”,山里木材多,如果自己家里需要木材做家具门窗等等,有时还扛木头回去。
从我们村子去下坝溪的路上,很多房子,以及其他地方的很多房子,都是由很多像老义这样的挑担工们一担一担挑出来的。
只是现在,很多这些山村里的房屋,都没有什么人居住了,因为很多人都往山外搬迁了。
只有这些屋前的弯弯延绵的山路,记得当初有无数个沉重的脚步,为了赚到几角钱,在它的身上迈走。
采茶黄柏梓摄 岁月记忆中的“双抢” □骆有云 1978年7月,是“文革”后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择优录取入学的第一个暑假,我从师范回到农村老家消暑度假。
当天晚上,担任生产队长的父亲便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眼下正是夏收夏种的农忙季节,生产队劳力少、农活忙,你可别闲着。
” 我是地道的农家子弟,若不是改革开放,赶上恢复高考制度的好机遇,自然是别无选择地一辈子铁心务农。
俗话说,饮水思源,故土难离,根本难忘,农民情结总是深根蒂固。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父亲便吹响哨子,招呼大家下田收割稻子。
乡亲们见到我,便纷纷围上前来,热情洋溢地嘘寒问暖,笑谑我这个“白面书生”怎么又下田了。
我笑着告诉大家:眼下正是夏收夏种的“双抢”季节,理所当然地要帮忙。
这叫“翻身不忘本”;何况 利用暑期挣些劳动工分,也可为家里减轻些负担,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么? 由于在师范学校呆了一学期,我变得有些细皮嫩肉,开始下地干活时,觉得有些不适应,在高温下劳作,累得腰酸背疼。
但过不了不久,我便慢慢地适应了这繁重的体力劳动。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拨乱反正,治理整顿,发展生产,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
我在劳动之余,也常和乡亲们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当时很明显的一种迹象已初露端倪:一些头脑灵活的社员隔三差五地私自外出做点小生意什么的,当生产队长的父亲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自然了。
繁忙而劳累的暑假一晃而过,9月1日离家回校时,我查阅了暑假的劳动工 分账目:出工47天,工分1412分。
当时我们生产队每10分的分红值为0.26元,我整个暑假的劳动收入折合人民币为36.71元。
新学期开学,我回到师范学校,满脸黝黑,像个黑炭头。
当时有位同学笑谑我说,暑期是不是去非洲旅行了?我闻之笑而不语,调侃自己曾与骄阳、农稼、汗水、疲惫有过亲密接触。
其实,当时凡家在农村的学员,莫不如此,这是很平常的事。
隔年,农村便逐步实施土地承包责任制。
那年暑假,我起早贪黑,日夜劳作,尽管累得精疲力尽,但心情却十分愉悦。
岁月如流,往事似烟。
一晃30年过去了,每当我回首当年暑假参加夏收夏种“双抢”劳动的往事,总是感慨万千。
生命中的那些往事会折射出特殊历史时期的光点,给人留下美好而难忘的记忆。
捉土猴记趣 □潘伟斌 自从在县城工作后,我就很少回乡。
偶尔回乡,也是来也匆匆走也匆匆,没好好品味家乡的泥土芳香。
而这种泥土香,是我童年再熟悉不过的。
细细梳理脑海中的记忆,童年的乐趣挺多的,捉土猴就是其中的一项。
土猴,是潮州话对一种像蟋蟀的小动物的叫法。
它的身体是黄白色,遍身光滑,细看有点像猴的模样,我想,这大概就是潮州人称之为“猴”的原因。
它属“油葫芦”一类蟋蟀科的害虫。
捉土猴,人少显得孤单,人多又觉 碍事。
三二小孩最佳。
找一个清朗的日子,三二小孩各带捉土猴的工具,有的手执玻璃瓶,有的捎带一纸盒,可作关土猴之用,夸张的还带一小木桶。
然后,就直奔战场,或是山坡,或是田埂。
土猴的特性是穴洞而居。
找到风水宝地之后,它就会掘洞。
工程做完后,洞口处用黄土掩盖。
像是一扇大门,保卫它的领地。
可惜,它的这扇大门是优点又是缺点,它让我们很快就找到它的家,因为洞口处掩盖的黄土是新土,这是识别土猴家居的方向性的指标。
找 到土猴的家,下一步就要把它从洞里逼出来。
于是,我们带来的玻璃瓶就发挥作用了。
把装满水的玻璃瓶倒置,嘴口对住洞口,隔不了多久,一只喝满了水胀着肚子的土猴就会从洞里爬出来。
如果找到土猴的洞口,但水源离得太远,这时小木桶就起了作用。
二个小伙伴发挥团体精神,合力把远处的水源抬回来。
有时灌土猴,也会有上它的当的时候。
找到土猴的洞口,放水进攻,可老半天,却不见土猴出来。
原来,这是土猴弄虚作假,做了一个假的住所,它真正的住所在别处一个洞穴。
可土猴这一招并不高明,它更激起我们的“义愤”,发誓要把狡猾的敌人揪出来。
当然,结果是我们大获全胜。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的童年没有电脑可上网,没有喜羊羊可作伴。
但这种亲近土地的童趣,别有一番生气。
老老伙伙计计你你还还好好吗吗?? □邬时民 现在我有一辆自行车,放在小区的家门口,不经常用。
因为交通很方便,走出小区就有公交车,如果要图方便,搭乘一下女儿的私家轿车也无妨,因此自行车也就成了“闲置品”,只是偶尔骑一下,权当健身。
可是,在30多年前,一辆自行车的用处可大哩。
记得那是1973年,我在浙北农村已经生活了5年。
考虑到可能要“插队落户干革命”一辈子,父亲托人搞到一张自行车票子,为我买了一辆28寸的凤凰牌载重车。
买来自行车的那天晚上,我兴奋得整整一夜没有入睡,那辆200多元的自行车足足花了父亲3个月的工资。
要知道,别说在农村,当时就是在城市,自行车也是普通人家的“奢侈”品。
当自行车通过轮船托运到乡下后,一下子引来了乡亲的纷纷围观。
世代以舟代车的水乡农民,从来没有“零距离”接触过自行车,所以个个都伸出手来,或摸摸自行车车把,或摸摸车身。
当我当场骑自行车“演示”的时候,竟然引来了乡亲们的阵阵欢呼。
当然,自行车给我带来了不少欢乐。
当别人肩上挑着100多斤稻谷到碾米厂碾米的时候,我却把稻谷放在自行车后座上,风驰电掣般地骑向碾米厂,半小时的步行路程,我只需用10分钟就够了,而且轻松自如。
更让我得意的是,有一次农闲的时候我去镇上茶馆喝茶,想不到村上的“村花”主动向我“抛出绣球”,要跟我一起到镇上“潇洒”一番。
君不知,当我带着漂亮姑娘去镇上时,沿途10多公里的路程不时听到羡慕声“:这小子可好福分,后面坐着的姑娘多漂亮!”说老实话,听了此言心里比吃了蜜糖还甜。
然而,自行车也给我带来过“烦恼”。
那时乡村没有石板路,都是泥路,有的地方甚至只有田间土埂,有的地方只有河堤,一方临河,另一方下面是水田,在这样的情况下,骑车若有不慎,就有可能跌入田间或者河中。
曾经有一次,我在河堤上骑车,车把一歪,结果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倒在下面的水田中。
还好,当时田间有水,总算没有摔坏人和车。
可是,当我扶着自行车重新上河堤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天哪,今天是往左边摔,假如往右边摔就完蛋了,下面是数米深的河水,尽管我会游泳淹不死,但是自行车沉到河底不就“暗无天日”了吗?所以,以后每逢经过河堤,只得推着走,在狭窄的路段,就来个“车骑人”,把自行车扛在肩上。
无疑,这样的举动难免会“夺人眼球”,让田间劳动的农民找到“笑柄”。
更让人“烦恼”的是,时常会有青年农民借我的自行车学骑车,学会了还要借用一下。
每每此时总是心想:哎,咱这可不是公车啊,是老爸的血汗钱换来的。
但是,作为“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为了能让贫下中农留下好的印象,只能“无条件”借给村民。
不怕你讥笑,每次借车人还车后,我总是仔仔细细地检查一下,车身若有一点擦痕,比自己身上擦破皮肉还要难过。
就这样,这辆自行车陪伴了我6年,当我在1979年秋季返城的时候,曾想带回它,由于随身行李太多,终于把它留在了我的“第二故乡”。
后来,因为工作繁忙,我一直没有回过乡下。
不过,我的心里时时在想:30年了,我的老伙计———28寸凤凰牌载重车,你还好吗?
二 http押//www.chaozhoudaily.com 温暖的手掌 □程毅飞 每当看电视看到父母不辞辛劳教养子女的镜头时,我就忍不住会想起父亲那温暖的手掌。
小时候,从我记事时起,家里的日子一直就很清苦。
虽然父亲是赤脚医生,收入比别的人家稍好一些,但生产队分的那点口粮还是不够吃,父亲总是在诊完病后,东坡跑到西坡地寻野菜,拿回家让母亲掺上一点点面粉蒸熟让我们吃。
我让父母跟我们一块吃,他们总是摆摆手说:“我们已经吃过了......”可我从父母那困乏无力的神态中知道他们是在哄骗我们。
一次放学回家,村头摆放着一个外乡人进村卖东西的挑担,见四下无人,我就随手拿了一根麻花,跑回家想给父母吃。
父亲问我:“麻花是从哪儿弄的?”我说:“别人给的。
”父亲不信,说:“你小小年纪就学会撒谎了。
今儿你要是不说实话,爹就不吃你给的麻花。
”我想让父亲吃了那麻花,就实话告诉了他。
谁知,当他听到麻花是从别人那里偷来时,一把拽住我的衣领,狠狠给了我一个耳光,又把我带到卖麻花人跟前,一边让我把麻花还回去,一边向那人道歉:“是我家孩子拿了你的麻花,小孩子不懂事,都怪我平日没管教好!”看到父亲低声下气的样子,我悔恨极了。
回到家中,父亲的气还没有消尽,在我的屁股上又抽了几个巴掌,然后罚我跪在场院边的核桃树下。
他在院旁一边沤着猪粪,一边发出阵阵叹息声。
看到父亲伤心的样子,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哽咽着说:“爹......我错了,以后......”父亲放下手中的铁耙,用他那宽厚的手掌捧着我的脸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呀,你要永远记着,咱人穷,可志不能短啊!”我扑在父亲怀里哭了起来,一向刚强的父亲一边用他粗糙的手掌给我擦眼泪,一边抱着我也哭了。
后来,土地承包到户,吃的不愁了,父亲多年紧锁的眉头也舒展了。
为方便村民就医,他在村口办起了医疗站,规模虽小,但药品还算齐全。
对来买药的村民,他都是按药品的进价售出,从不赚乡亲们一分钱。
村里的孤寡老人和家庭困难户有个头疼脑热,他都会主动带上药物上门给他们诊治,从来不提钱不钱的,有的人家给钱让急了,父亲最多只收一半的药费。
为此母亲还跟父亲吵过几次嘴,我也在父亲面前表示过不满。
父亲也不发火,拍拍我的脸蛋说:“孩子,与人为善,这是做人的本分,你爹能当上村赤脚医生,就是大家在抬举咱们,你说爹不为他们着想为谁着想?”我觉得父亲的巴掌轻轻的、暖暖的。
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父亲别提有多高兴了,整天进进出出脸上都挂着笑,他说要让村里的乡亲来家聚一聚,既是感谢大家,也是向我表示祝贺。
可谁曾想,事情还没有开始操办,小妹却得了病,父亲和大哥只好带着小妹去省城的大医院治疗。
临出门,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儿呀,爹对不住你,等以后有时间再给你补上,我和你大哥这一走可能得十天半月的,家里就交给你了。
”说完,他就走出了家门,我看到父亲眼 里有泪花在闪,隐隐觉出小妹的病可能不轻。
快入学的时候,父亲一个人回来了,仅仅半个月时间,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整个人似乎也老了许多。
我问小妹的病怎么样,他只是说没什么大碍,让我不要操心,只管上学就是。
那一夜,我闹肚子经过父母的窗下,听到他们谈话,才知道小妹得的是胃癌,已经是晚期,在省城住院花光了家里的钱,父亲这次回家一是借住院费,二是想办法让我尽快去上学。
他们不想让我知道实情。
我听到父亲在不停地叹息,母亲也在低声地哭泣着。
第二天,我醒来没见着父亲,只看到母亲的眼泡肿涨得很高,问她,她说父亲天不亮就出了门。
我知道他是去借钱了。
快到吃饭的时辰,父亲回来了。
我走上去对他说:“爹,我不想上大学了,我想出去挣钱。
”听了我的话,父亲额头的青筋一根根暴了起来,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对我吼道:“你说啥?你再给我说一遍!”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见到父亲那样发过凶,就躲进里屋大声哭了起来,母亲也陪着我流眼泪。
看到这情形,父亲走过来心平气和地说:“有难处有啥怕,想想办法能挺过去的,不是还有乡亲邻里们帮忙吗!”说着,他就把一个纸包交到了母亲手中。
两天后,我踏上了上学的路,父亲送我到县城,又把我送上了去远方的客车。
临别时,他把一个装有2000元钱的牛皮纸袋交给我,说:“到了学校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一片心意。
饭一定要吃饱,正在长身体,不要搞坏了身子。
钱不够了就给家里写信,爹给你寄......”他一边说着,手不停地抚着我的脸。
车要开了,他却抓着我的双手久久不愿放开。
小妹终于没能留住,她还是走了,那年她才刚刚16岁。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父亲送我去县城的时候,小妹已经不行了,父亲是知道的,可他瞒着我。
这时我才明了,父亲那天为什么久久抓着我的手不愿放开。
坚强的父亲是怎样忍着内心的悲痛目送我离去的呀……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县城工作。
我加倍努力,想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可是,天不遂人愿,不久父亲就查出患有与小妹同样的病,而且也是到了晚期。
我和大哥要送他去省城治疗,可他说什么也不肯,我们逼急了,他就说:“我知道我得的是啥病,没用的,不要瞎糟蹋钱了,害得你们以后背一身的债,那样,就是我死了也不会闭上眼睛的。
”无奈,只得用药物保守治疗。
油尽灯灭。
父亲终究没能挨过那个寒冷的冬天,在腊月初一离我们而去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父亲把我们叫到身边,看着我们一句话也不说,用手不停地抚摸着我和大哥的头。
我依在父亲身边,紧紧攥住他瘦如干柴的双手,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泪水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
如今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对父亲的思念却愈加强烈。
每每想起,总有一双宽厚的巴掌在我心里抚来摸去,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温暖。
父亲与草鞋 □莫文勇 父亲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一生爱穿草鞋。
记得十三岁那年冬天,我看见父亲的脚被冻得皲裂流血,仍然穿草鞋。
我不解地问“:天这么冷,您怎么还穿草鞋?”父亲动了动嘴唇,欲言又止。
晚上,父亲拿出一件东西,是用牛皮纸包着的。
他神情严肃,慢慢拆开了牛皮纸包,里面的东西还用红布包裹着。
在我们乡间,只有很珍贵的东西才用红布包起来珍藏。
我心想:这究竟是什么宝物呢?红布打开了,竟是一双将要穿烂的草鞋,因年久,已经变色,还带有点霉味。
我惊讶地问父亲“:您怎么把一双旧草鞋这样藏起来?”见我疑惑,父亲慢慢讲述了他与草鞋的情缘。
解放前夕,父亲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被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
他不愿为旧军队卖命,没过几天便在一个夜晚逃了出来。
怕被抓回去,他只得扔掉一身军装,光着脚在荆棘丛生的大山上朝着家乡的方向逃跑。
脚腿不时被刺伤、划破,痛苦不堪。
走着走着,不知到了悬崖边,父亲一脚步踩下去,一根尖利的木桩刺进了脚心,钻心透骨般疼痛。
他一收脚,便一个踉跄跌下悬崖,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日头偏西。
他满身是伤,脑壳发晕,又饥又渴,无力动弹了。
在那荒山密林中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想到远在家乡的父母,禁不住伤心落泪。
正在父亲绝望之时,来了一对上山捡柴的农家婆媳。
见了我父亲,问明缘由后,把我父亲背回她家医治养伤,直到伤愈。
临别时,大娘拿出一双崭新的草鞋,对父亲说:“穿上,免得又伤了脚……”父亲穿着新草鞋,循着老大娘指的路,终于逃回了家。
一回到家,他就把这双草鞋珍藏起来。
我恍然大悟,终于第一次“读”懂了父亲脚上草鞋的价值。
我上高中时,母亲早已去世。
父亲年逾花甲,又当爹又当妈,日夜操劳供我读书。
一个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我们学生关着教室的门窗读书。
第一节下课时,我刚走出教室就看见父亲走来。
他脚上穿着一双崭新草鞋,双脚冻得发红,还裂开大大小小的口子,流着血丝。
我鼻子一酸,心里一阵难过。
父亲却笑了笑先开口:“天气这么冷,我想你没有菜钱了,给你送来两块钱,又带两件旧衣服来,好加在身上。
”老家离学校五十多里,父亲竟来得这么早,我问:“坐车来的?”父亲说:“天未亮就动身来学校。
”我心里一酸,泪水盈满了眼眶。
我从父亲手中缓缓接过那还带着父亲体温的两元钱,感到异常沉重。
“好好读书吧,我走了。
”父亲说完,转身就走了。
望着穿着草鞋的父亲远去的背影,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山路弯弯 □路边青草 小余是我的一位小学同学,他家在一个叫下坝溪的地方,那是离我的村子有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山中小村。
前些天假日,我们都从外面回老家,小余约我一块去他的山里老家下坝溪玩,因为眼下正是他们老家山上杨梅熟的时节,我们上山摘杨梅去!去下坝溪摘杨梅回来,碰到村子里的曾奶奶,那是一位八十岁的老阿婆。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了,她遇到我自是很亲切,问了很多话,我说我去下坝溪摘杨梅回来呢。
我又问:“曾奶奶,你去过下坝溪吗?” “去过,但离现在都四十多年了。
我去得少,老义去得多,同行的经常都有十多人,那都是我们村里的青壮男子。
” 曾奶奶说的老义,是她的老公,不过已经去世多年了。
“大家去那里做什么呢?”“那时大家都过得辛苦啊,去下坝溪找饭吃,就是———挑担。
”“挑担?”“就是帮人挑东西,天天挑一担东西,往返于我们村里与下坝溪之间。
”“挑什么东西呢?”“挑石灰。
”于是,曾奶奶与我聊起了当年的事情。
人要生活,总得有居所,要建房屋,就少不了原材料。
下坝溪是山村,所需要的建筑材料,都是从山外买进去的,那时的交通和运输都落后,汽车根本是没有的,即使有 车,山路太小也是行走不了,所需的水泥砖瓦石头石灰,完全是靠人工一担一担挑运,而大家把给别人挑运东西,叫做“挑担”。
其实不仅仅是下坝溪,很多山里山外的大小村子建造房屋,所需的材料都是靠人挑运的。
老义是我们村里挑担的领头,因为那时大家都要去生产队集体劳动干活,只有闲余的时候,才能偶尔去挑一下担赚点外快。
但老义不去生产队干活,专职的“搞副业”,因为没有去生产队劳动,所以每个月要向生产队交36块钱的“副业款”。
下坝溪离得远,来回50公里路。
人的走路速度一个小时是一铺路(5公里)左右,十铺路,得走上十个小时。
即使空手连续走上十个小时的路,人也是会累、并且越走越慢的,何况身上还要挑一百斤重的东西呢!半路上歇息和耽搁的时间,自是不少的了,到了目的地,和买主又少不了交谈和喝水的时间。
所以,这十铺挑担路,真是“出门黑天,回家天黑”。
在黑夜中行走的路程也很长。
山间的晚上可不像城市里的晚上,山间要是没有星星和月亮的话,则是完全彻底地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挑担的人,便要举着火把照明。
照明的火把,可不是点的汽油煤油,而是竹子。
去山上砍来一种小竹子,把它们砸扁,在水池里浸泡上半个月,再捞起晒干后,易燃也耐燃。
挑担时通常都有伙伴,所以挑担的人,每个人除了挑上百斤的石灰 重担,和路上吃喝的干粮茶水外,每个人同时也都还得携带上几斤的干竹子以供照明,你的点完了就点他的,他的烧完了,就点另一个人的。
如果竹子没有烧完的话,则扔在路上,晚上回家的时候,又可捡来点着照明用。
曾奶奶那时才30多岁,还很年轻,每天也去生产队干活,有空的时候,头天便去镇上石灰厂买回一担石灰挑回来,算是减轻一下老义的工作量,老义第二天便把这担石灰挑到下坝溪去。
曾奶奶没有空的时候,则要老义自己去石灰厂买,镇上的石灰厂离村子也有五六公里路,需要老义自己去购买石灰的时候,这又得花去很多准备时间,则当天是不可能去下坝溪的了,得等到第二天再挑出门。
所以一个月下来,即使你是铁人,通常只能往返15担左右,最多的时候,也只是20担。
石灰挑到了下坝溪,买来是6角钱一百斤,卖价是3元钱,也就是一百斤有2元4角钱的利润。
一个月如果挑了15担一百斤的,一担赚2元4角,则赚到36元,刚好够交给生产队作副业款,自己就一分钱也不剩了。
一个月如果挑到20担,则可赚到48元,减掉交给生产队的,一个月下来能赚到12元钱。
很多人其实挑不到一百斤的石灰,只能挑到七八十斤,但加上扁担竹篓、竹子火把、干粮茶水,总重量也是上百斤了。
为了多挣钱,老义的挑担重量,经常都有一百三四十斤。
老义赚到的钱,通常一个月就是10块钱左右。
10块钱,可以买几十斤的粮食和应付一些油盐柴火等开支了,但这可是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啊!老二养了五个小孩子,还有父母,一家人吃的饭量可说是很不小的。
那时的大米价格,国家卖的是1角4分钱一斤,因为粮食紧缺,去买黑市的大米的话,价格则要6角钱一斤。
所以老义接的活计,一天也断不得,因为接的活计一断,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不能向生产队交钱,也不能维持自己家里吃用开支了。
其实,他做熟了,活是长年都不缺的,这里的活计接完,马上有下一个活接。
因为建房子所需的材料,毕竟不是一担两担能解决的,一个人挑一担往返时间需要一天,一个月下来也只能挑到十几担,对建房子来说远远不够,所以接到一个活,一个人还经常忙不过来,老义便经常叫上村里的人一块去挑担“赚钱”。
除了“赚钱”,有时也“赚物”,山里木材多,如果自己家里需要木材做家具门窗等等,有时还扛木头回去。
从我们村子去下坝溪的路上,很多房子,以及其他地方的很多房子,都是由很多像老义这样的挑担工们一担一担挑出来的。
只是现在,很多这些山村里的房屋,都没有什么人居住了,因为很多人都往山外搬迁了。
只有这些屋前的弯弯延绵的山路,记得当初有无数个沉重的脚步,为了赚到几角钱,在它的身上迈走。
采茶黄柏梓摄 岁月记忆中的“双抢” □骆有云 1978年7月,是“文革”后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择优录取入学的第一个暑假,我从师范回到农村老家消暑度假。
当天晚上,担任生产队长的父亲便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眼下正是夏收夏种的农忙季节,生产队劳力少、农活忙,你可别闲着。
” 我是地道的农家子弟,若不是改革开放,赶上恢复高考制度的好机遇,自然是别无选择地一辈子铁心务农。
俗话说,饮水思源,故土难离,根本难忘,农民情结总是深根蒂固。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父亲便吹响哨子,招呼大家下田收割稻子。
乡亲们见到我,便纷纷围上前来,热情洋溢地嘘寒问暖,笑谑我这个“白面书生”怎么又下田了。
我笑着告诉大家:眼下正是夏收夏种的“双抢”季节,理所当然地要帮忙。
这叫“翻身不忘本”;何况 利用暑期挣些劳动工分,也可为家里减轻些负担,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么? 由于在师范学校呆了一学期,我变得有些细皮嫩肉,开始下地干活时,觉得有些不适应,在高温下劳作,累得腰酸背疼。
但过不了不久,我便慢慢地适应了这繁重的体力劳动。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拨乱反正,治理整顿,发展生产,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
我在劳动之余,也常和乡亲们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当时很明显的一种迹象已初露端倪:一些头脑灵活的社员隔三差五地私自外出做点小生意什么的,当生产队长的父亲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自然了。
繁忙而劳累的暑假一晃而过,9月1日离家回校时,我查阅了暑假的劳动工 分账目:出工47天,工分1412分。
当时我们生产队每10分的分红值为0.26元,我整个暑假的劳动收入折合人民币为36.71元。
新学期开学,我回到师范学校,满脸黝黑,像个黑炭头。
当时有位同学笑谑我说,暑期是不是去非洲旅行了?我闻之笑而不语,调侃自己曾与骄阳、农稼、汗水、疲惫有过亲密接触。
其实,当时凡家在农村的学员,莫不如此,这是很平常的事。
隔年,农村便逐步实施土地承包责任制。
那年暑假,我起早贪黑,日夜劳作,尽管累得精疲力尽,但心情却十分愉悦。
岁月如流,往事似烟。
一晃30年过去了,每当我回首当年暑假参加夏收夏种“双抢”劳动的往事,总是感慨万千。
生命中的那些往事会折射出特殊历史时期的光点,给人留下美好而难忘的记忆。
捉土猴记趣 □潘伟斌 自从在县城工作后,我就很少回乡。
偶尔回乡,也是来也匆匆走也匆匆,没好好品味家乡的泥土芳香。
而这种泥土香,是我童年再熟悉不过的。
细细梳理脑海中的记忆,童年的乐趣挺多的,捉土猴就是其中的一项。
土猴,是潮州话对一种像蟋蟀的小动物的叫法。
它的身体是黄白色,遍身光滑,细看有点像猴的模样,我想,这大概就是潮州人称之为“猴”的原因。
它属“油葫芦”一类蟋蟀科的害虫。
捉土猴,人少显得孤单,人多又觉 碍事。
三二小孩最佳。
找一个清朗的日子,三二小孩各带捉土猴的工具,有的手执玻璃瓶,有的捎带一纸盒,可作关土猴之用,夸张的还带一小木桶。
然后,就直奔战场,或是山坡,或是田埂。
土猴的特性是穴洞而居。
找到风水宝地之后,它就会掘洞。
工程做完后,洞口处用黄土掩盖。
像是一扇大门,保卫它的领地。
可惜,它的这扇大门是优点又是缺点,它让我们很快就找到它的家,因为洞口处掩盖的黄土是新土,这是识别土猴家居的方向性的指标。
找 到土猴的家,下一步就要把它从洞里逼出来。
于是,我们带来的玻璃瓶就发挥作用了。
把装满水的玻璃瓶倒置,嘴口对住洞口,隔不了多久,一只喝满了水胀着肚子的土猴就会从洞里爬出来。
如果找到土猴的洞口,但水源离得太远,这时小木桶就起了作用。
二个小伙伴发挥团体精神,合力把远处的水源抬回来。
有时灌土猴,也会有上它的当的时候。
找到土猴的洞口,放水进攻,可老半天,却不见土猴出来。
原来,这是土猴弄虚作假,做了一个假的住所,它真正的住所在别处一个洞穴。
可土猴这一招并不高明,它更激起我们的“义愤”,发誓要把狡猾的敌人揪出来。
当然,结果是我们大获全胜。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的童年没有电脑可上网,没有喜羊羊可作伴。
但这种亲近土地的童趣,别有一番生气。
老老伙伙计计你你还还好好吗吗?? □邬时民 现在我有一辆自行车,放在小区的家门口,不经常用。
因为交通很方便,走出小区就有公交车,如果要图方便,搭乘一下女儿的私家轿车也无妨,因此自行车也就成了“闲置品”,只是偶尔骑一下,权当健身。
可是,在30多年前,一辆自行车的用处可大哩。
记得那是1973年,我在浙北农村已经生活了5年。
考虑到可能要“插队落户干革命”一辈子,父亲托人搞到一张自行车票子,为我买了一辆28寸的凤凰牌载重车。
买来自行车的那天晚上,我兴奋得整整一夜没有入睡,那辆200多元的自行车足足花了父亲3个月的工资。
要知道,别说在农村,当时就是在城市,自行车也是普通人家的“奢侈”品。
当自行车通过轮船托运到乡下后,一下子引来了乡亲的纷纷围观。
世代以舟代车的水乡农民,从来没有“零距离”接触过自行车,所以个个都伸出手来,或摸摸自行车车把,或摸摸车身。
当我当场骑自行车“演示”的时候,竟然引来了乡亲们的阵阵欢呼。
当然,自行车给我带来了不少欢乐。
当别人肩上挑着100多斤稻谷到碾米厂碾米的时候,我却把稻谷放在自行车后座上,风驰电掣般地骑向碾米厂,半小时的步行路程,我只需用10分钟就够了,而且轻松自如。
更让我得意的是,有一次农闲的时候我去镇上茶馆喝茶,想不到村上的“村花”主动向我“抛出绣球”,要跟我一起到镇上“潇洒”一番。
君不知,当我带着漂亮姑娘去镇上时,沿途10多公里的路程不时听到羡慕声“:这小子可好福分,后面坐着的姑娘多漂亮!”说老实话,听了此言心里比吃了蜜糖还甜。
然而,自行车也给我带来过“烦恼”。
那时乡村没有石板路,都是泥路,有的地方甚至只有田间土埂,有的地方只有河堤,一方临河,另一方下面是水田,在这样的情况下,骑车若有不慎,就有可能跌入田间或者河中。
曾经有一次,我在河堤上骑车,车把一歪,结果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倒在下面的水田中。
还好,当时田间有水,总算没有摔坏人和车。
可是,当我扶着自行车重新上河堤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天哪,今天是往左边摔,假如往右边摔就完蛋了,下面是数米深的河水,尽管我会游泳淹不死,但是自行车沉到河底不就“暗无天日”了吗?所以,以后每逢经过河堤,只得推着走,在狭窄的路段,就来个“车骑人”,把自行车扛在肩上。
无疑,这样的举动难免会“夺人眼球”,让田间劳动的农民找到“笑柄”。
更让人“烦恼”的是,时常会有青年农民借我的自行车学骑车,学会了还要借用一下。
每每此时总是心想:哎,咱这可不是公车啊,是老爸的血汗钱换来的。
但是,作为“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为了能让贫下中农留下好的印象,只能“无条件”借给村民。
不怕你讥笑,每次借车人还车后,我总是仔仔细细地检查一下,车身若有一点擦痕,比自己身上擦破皮肉还要难过。
就这样,这辆自行车陪伴了我6年,当我在1979年秋季返城的时候,曾想带回它,由于随身行李太多,终于把它留在了我的“第二故乡”。
后来,因为工作繁忙,我一直没有回过乡下。
不过,我的心里时时在想:30年了,我的老伙计———28寸凤凰牌载重车,你还好吗?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