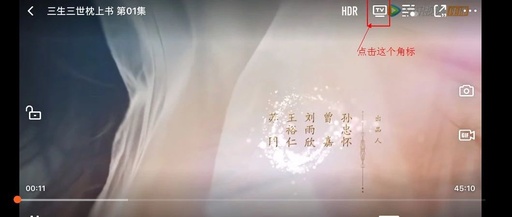星期
五 青书画B7 展览:万籁展期:2022.4.29-7.31地点:南京金鹰美术馆 万籁之中当有你的声音◎刘婷 电梯很快到达52层。
站在200米高的金鹰美术馆俯瞰整座南京城,能看到很多车子在缓行,人像小蚂蚁一般挪动,但听不到窗外任何声音,他们只是在静静地流动。
这时候你会明白何谓“万籁俱寂”。
而我则将在这个万籁俱寂的地方看一场名为“万籁”的展览。
我是有期待的。
我曾在乌镇2019当代艺术邀请展艺术节上看到过雅娜·文德伦在乌镇水下录制的鲤鱼吐泡泡的声音(《隔骨传音·与鲤鱼一起聆听》),那很梦幻,也很浪漫。
我自己也曾在山间录制流水的声音,在夏日雨后河边记录蛙鸣,也曾在夏天日光很烈的时候,于山间林下,听取聒噪蝉鸣。
所以在“万籁”展上,我以为自己会听到山林的喧嚣,自然的虫唱。
对于我们这些由于疫情只能久居城市钢铁丛林的人来说,这将会是一场怎样的温暖之旅? 然而这些都没有。
这种冲击是直接的,就像你本来期待的是农家菜,突然上来了一桌法式大餐。
虽然预期落空,却也别有趣味。
走进第一个展厅,南京的城市元素扑面而来,六朝古都兴衰,千年文化脉络起伏。
历史学家用史笔描摹人物生平,小说家用想象场景呈现历史细节,诗人则发内心之幽情,那么声音又能做什么呢?展方选择了四段声音:魏晋古语朗诵的梁武帝萧衍《河中之水歌》、宋时古语念白的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英语诵读的《拉贝日记》片段,以及带有未来气息的科幻小说《我们生活在南京》的电波声。
四段声音都与南京有关,从古代到未来,声音背后是有景象的,闻声如见景,听音如在场。
你好像同萧衍一起在河中游荡,好像与辛弃疾一起拍了栏杆,仿佛置身于1937年那个残酷战争场景,又好像陷入到未来的慌乱未明状态之中。
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能够活化历史时期人们说话的方式,但这并不是最令人惊奇的,最让我感动的是未来的那段声音,嘈杂的无线电湮没了人声,让人有一种置身于赛博空间的感觉。
未来,声音或许会回归到一种纯粹的波的形式,带有确切含义的语言则会退居其次,甚至消失。
与四个听筒相对的是窦平平的《檐下耳语》装置,她企图以声音的形式转化文学内容,当你坐下去的时候,文学在你耳边低语,当你离开,声音随之消失。
这像是一个隐喻,有些声音,只有去听才能听到,就像我们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我们也永远无法对那些不想听我们说话的人说些什么。
沿着长长的走廊深入,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声音装置:红色帷幔之中是波浪一般起伏的钢丝结构物,其灵感来源于藏族的经幡。
古老的藏族文化,背后隐藏着关于 抚平心灵的秘密方式,装置恰 好构建了一个冥想和聚集的场所,其下方是一片镜面,象征着水。
水是平和的,水是随物赋形的,它将这种哲学韵味推向了极致。
进入装置内部,风声水声交错着人声,内部的铜铃亦随之摇曳,人因此而进入梵境。
延续这种梵境的是OPEN建筑事务所的《山谷音乐厅》的声音作品。
作品位于一个暗房之中,当我拉开帷幕,小心进入,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悬崖,风景不断变化,山、石、植物、空旷的场景等在眼前变换,之后是山谷音乐厅。
它是真实存在的,位于承德的山区,以一种空灵的、仿佛天外来物的姿态存在。
舒缓的钢琴曲从视频中流出,经春历冬,山野的景致随四时不同而如走马灯一般变化。
当我坐在屏幕前,仿佛坐在了山间,屏息聆听自然的呼吸,飘雪声、风声,以及山间特有的动植物的声音,声声入耳、入心,我与这一切融为了一体。
“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
”《淮南子》如是说。
离开山谷音乐厅,穿过遮光帘,我一下子进入了“宇宙”。
一个夺目光滑的六面体建筑出现在眼前——宇宙八音盒,这是一个企图实现人与宇宙在声音层面上实时互动的乐器。
在八音 盒两边墙面张贴着屏幕,其上播放着人类探索宇宙的场景和声音——“4、3、2、
1,点火!”人是宇宙的结晶,同时人也感受着来自宇宙的讯息。
通过声音的方式,人与宇宙相互交流。
我们听到了宇宙的波声,宇宙是否也能听到我们的八音盒里传达出来的声音呢? 在“宇宙”的隔壁,依旧是用厚重的遮光帘作为隔断,暗黑的空间里一块屏幕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初看时以为是梵高的《罗纳河畔的星夜》,坐定了发现,镜头在向前缓缓移动。
在南京声音地图项目所创作的《秦淮音河24小时》里,我们随着紧贴河面的视角,身临其境般地在秦淮河里徜徉,聆听着这座城市古老而现代的声音。
城市永远在更新,古老的城墙则只是 默默矗立。
市井永远是鼎沸的,流 水的潺潺却引人入梦。
这构成了一幅当下南京城的图像,与展厅一开始的过去的南京、未来的南京,形成了呼应。
声音一直在变化,变化的主导者是人,人享受着声音的美感和形式,人赋予了声音不可思议的想象空间,人试图用声音呈现我们所在的时空。
所以走出展厅,进入另外一个长廊,看到鲁安东(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殷漪的《三声庭》展览现场会有一种文末总结的感觉。
“我听故我在”的展签,是野心,也是一种宣言。
步出展厅,余音绕梁,同时我也在思考,一场以声音为主题的展览该是怎样的? 人其实是视觉动物。
视觉所带来的感官冲击永远是最强烈的。
卢梭曾论述过,眼睛能比耳朵接纳更多的感知对象,因此对眼睛说话比对耳朵说话更有效。
所以在人类之中形成了一种“眼睛”即“正义”的文化传统,中国人也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表现在当代艺术的展览里,视觉往往多于听觉,也往往比听觉更重要。
音乐或其他声音形式只是视觉展览的一种信息要素的补充,是一种辅助手段。
有声会更好,没有也不要紧——我们常常是这种感觉。
这不就是短视频的算法推 荐吗?永远推荐我们喜欢的,最后我们便会一直生活在我们所喜欢的氛围之中。
而那些我们所不喜的,我们很少考虑它们的死活。
它们大概率的结局也会是死亡。
我们喜欢图像的,所以图像会天长地久,而声音的、文字的那些,就会慢慢退却,直至消失。
声音是脆弱的。
儒家传统中“五经”本来是指诗、书、礼、乐、易。
其中唯独《乐记》消失了,因为它是和声音相关的文字作品,一旦隔代,后人就读不懂了,便不会流传下去。
嵇康之后再无《广陵散》,也因为它是声音的形式。
其实消失的声音,何止广陵散?我们的声音一直在消亡,大到整个地区的方言乡音,小到一个街区的叫卖声音,都是如此。
我想起外婆中气十足的声音,她总是喜欢说:“怕什么?有外婆呢!”我长大了的时候,外婆已去往另一个世界,她的声音好像还在耳边,但已经慢慢模糊,以至于不复记忆。
其实很多声音都是这样。
同时声音又是具有穿透力的。
有些声音令人不适,甚至令人害怕;有些声音令人深思,有些声音令人忘我;有些声音说不出哪里好,但就是会让我们动容不已;有些声音则成为我们记忆最深处的美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回荡。
我有时候想,声音之所以会有这种穿透性,也是因为它的绵软无力,恰好能够击中我们的内心。
一场以声音为主题的展览,是需要勇气的,是必要的,也是巧妙的。
或许从一开始它就没有想过要讨好观众,在一切都需要流量的时代,它难以成为网红展,那些抱着拍摄好看照片而去的观众,必定也会铩羽而归;但那些带着聆听之愿而来的观众,一定会像我一样坐在《山谷音乐厅》的大屏面前,心归道山。
回答之前提到的那个问题:一场以声音为主题的展览该是怎样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有现成答案的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开放式问题。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有的人会把亲人的絮语放进去,有的人会把街头叫卖放进去,有的人会把流水声放进去,有的人则可能把吵架的声音放进去,有的人会展现自相矛盾的声音,有的人会用声音探索表达的尺度和空间问题……而我希望这样的声音探索,没有止境。
“万籁”之中需要每个人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
摄影/倪清蓉 在热情消退之前让我们愉快告别 城市里餐饮业重启堂食的那天,出门约友人吃饭,在出租车上经历了许久未见的堵车。
司机抱怨钱难赚和城市生活的无聊——除了吃饭、逛商场、看电影,就没什么别的娱乐项目了。
国际旅行尚不敢多想,远程出游也受限制,城市里先风靡起了精致露营。
人们热衷于寻找近郊新开发的商业露营地,在后备箱里装上按图索骥的月亮椅、天幕、户外炊具,随时准备奔赴人造“自然”——为测试新开封的新装备,在野外聚众烤肉、喝咖啡,同时不忘架起手机三脚架。
还是要怪城市娱乐生活太贫瘠。
即便是一场远途旅行,普遍而大众的方式也不过是订目的地,然后订车票、机票、酒店,一番舟车劳顿后,继续吃饭、逛景点、压马路、打卡、消费甚至露营……只是更换下俗世生活的背景幕布。
那么,一本关于“旅行”的书,要给人看些什么不一样的? “见没见过一个地方的朝霞和晚霞。
”这是作家韩松落衡量旅行的硬指标——需要在一个地方停留足够久,或者至少需要一些深度的体验,才能称之为旅行,否则只是路过。
《浪游记》的作者有三位:王恺、韩松落、尼佬。
前两位是作家、媒体人,前者多年前跑社会新闻,去了很多偏僻地采访;另一位西北人,写了很多影评、乐评和专栏文章;尼佬是给Lonely旅行指南供稿的职业旅行家。
行走各地、随笔记录是这三位的工作和习惯,来场“六手联弹”是媒体人王恺的发心,撺掇到一起,就成了这本跟一般旅行文学不 太一样的随笔集。
从读者的角度读旅行文学,若是看单 一作者预设目的、计划的行走记录,有时不免感到疲惫。
但读《浪游记》,更容易在心态上保持轻松——它的阅读体验有些OldSchool——有些像听一张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独立音乐合辑。
被其中一两篇文章惊艳到的感受,类似当年被某个乐队“一曲入魂”,像开启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
不知王恺老师策划这本合集的时候,是不是也从老唱片里获得了些灵感?1970、1980年代的人,还比较容易有些共同的影音记忆。
《浪游记》在文章编排上也很有意思:它不按时间、空间顺序组合。
篇章设计成“自在”“乡愁”“尘间”“味道”“温度”“遇见”“阅世”七个部分,这或许是传统媒体人策划组稿的思路,翻起来就像随便翻杂志。
这让读《浪游记》变成纯粹的闲读:点根香,台灯下读几篇;用脚撸着地毯上打滚的猫读个几篇;铅笔画画线,伏在案头再翻几篇。
两天,我就“浪”着翻完了。
从书店从业者半个内行的角度看,《浪游记》的纸质书做得相当考究:小32开+裸线书脊+外封的设计,内文用纸和排版的字号、字距,都考虑到了读者的阅读舒适度,小民老二的插画有种久违的野生气息,书里的横幅摄影都做成了对开跨页,又能打开铺平到180度……种种设计细节,都能看到轻盈、舒服、散淡背后的细心思。
想来也略感到遗憾,这本书所呈现的美好——纸刊、纸书、装帧、手绘摄影、认真走路……在全民数字阅读和短视频的 当下,都有些小众。
把一本关于旅行的纸书做到这份儿上,近乎于在传承手艺了。
另注意到一细节,《浪游记》的每篇文章,开篇不署作者名,这或是三位旅人面对世间风景的谦卑心——或许三位都认同这个观念:风景不是行走的背景,人对于自上古就存在的自然来说,没那么重要。
当写作者和读者的自我,都能隐遁于荒野之中,相逢纯属偶然中的偶然。
同为过客,能共一路风景,就聊上几句。
景见过了,话讲完了,也就该告别了。
结尾署名,是记录者的如是观照,像古人一句“属予作文以记之”。
“风格即一切。
”用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对写作者的评价标准来看旅行 者,也是一样的——Ta怎么走路,看些什么,体验什么,跟什么人交谈——组成Ta自己。
相信翻完整本《浪游记》的读者不会错识三位作者。
《浪游记》里的三位,身上都有可辨识特征:身怀古风、热爱荒野的西北人是韩松落;见多了生死悲欢、转向用玩心流连俗世的是王恺;特别能走路、爱喝啤酒的孤旅人就是尼佬。
三位交出的碎片记忆也各有风格:有人于童年溪水边拾得璞玉一块,深藏多年,却于离开故地之时将它扔下山坡,猜想它终将化作宇宙星辰,这是豁然;有人奔赴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因被尘世苦难触动,止步于穷街陋巷,这是悲悯;还有人徒步尼泊尔高原,一路鲜见青蔬油水,却又在离开之后,把村落的日照金山景色忘了,也忘不了旅程中最美味的豆汤饭,这是仁爱。
何为“浪游记”?精髓该在一个“浪”字。
王恺的诠释——“随心所欲,没有目的,经常走神。
”这寓意着接纳世界以本来的模式运行,接受别人的日常于自己的生活可能相悖,对不在期待之内的意外和必然保持包容。
也唯有这样,“游”才能自在。
设定了目的方位的景致,离人归乡的风景,采访路过的偏僻陌生地……若是不带分别心、不纠结于故乡他乡此处彼处,在当下所处的地方能身心合
一,周边的三公里乃至三十米就都有风景可见。
“记”则是随记,放任自己随意散漫地记下什么,让胸中块垒或快意弥散开来。
信马由缰地写,才不会被求成的欲望牵绊住。
可能放任自己去自由行走、体验的人 ◎绿川 毕竟还是少数,这也是为什么《浪游记》里写下的人和事,能让旅人有惺惺相惜之感。
你身边或许也有这样的朋友,就像书中《惊起千只白鹤》一篇提到的马格,他们并不从事什么文艺工作,他们只是不安于室,去一个地方不拍照片,也不写什么东西,甚至他们并不谈论旅行。
只有你跟他共桌吃过饭、喝到位的那些罕见时刻,才有机缘听到些惊人故事。
诚如王恺所言:“没有一次旅行,不是回到故乡。
”人们去往别处,看风景、闲逛、吃新鲜食物,和人交谈。
因为陌生景致充分调动感官,赋予自己身心合为一处的错觉,然后回到日常栖身之所,是为了能对贫瘠的日常多些耐受。
旅行总有终点,旅人总要告别,说起来人的尘世旅行,也就是在寻刺激和谋生存中来回摇摆着度过了。
印象深刻的一段,来自尼佬的伊朗旅程:他被酒店服务员(厨师)忽悠去爬5604米的达马万德——伊朗第一峰。
司机拉上去,给他两小时自由登顶时间,下山后在野外BBQ,吃鸡肉牛肉串和蘑菇串,喝伪啤酒、抽水烟,临行前那人又来推销包车去伊斯法罕,被他拒绝,写一段文字,极喜欢:“兄弟啊,我们有半天来抽水烟,已经是不错的缘分了。
一个习惯孤独的旅人,可以给陌生的路人微笑甚至眼泪,那也只是因为陌生而肆无忌惮地放空,在热情没有化作消耗之前,让我们愉快地再见吧。
”《浪游记》之于当下的意义,也就在此。
在我们囿于一地的当下,在纸上,读一些风吹过的旅程,就在热情未消退之时,我们告别。
编辑/史祎美编/巨琳责校/方立董一凡
五 青书画B7 展览:万籁展期:2022.4.29-7.31地点:南京金鹰美术馆 万籁之中当有你的声音◎刘婷 电梯很快到达52层。
站在200米高的金鹰美术馆俯瞰整座南京城,能看到很多车子在缓行,人像小蚂蚁一般挪动,但听不到窗外任何声音,他们只是在静静地流动。
这时候你会明白何谓“万籁俱寂”。
而我则将在这个万籁俱寂的地方看一场名为“万籁”的展览。
我是有期待的。
我曾在乌镇2019当代艺术邀请展艺术节上看到过雅娜·文德伦在乌镇水下录制的鲤鱼吐泡泡的声音(《隔骨传音·与鲤鱼一起聆听》),那很梦幻,也很浪漫。
我自己也曾在山间录制流水的声音,在夏日雨后河边记录蛙鸣,也曾在夏天日光很烈的时候,于山间林下,听取聒噪蝉鸣。
所以在“万籁”展上,我以为自己会听到山林的喧嚣,自然的虫唱。
对于我们这些由于疫情只能久居城市钢铁丛林的人来说,这将会是一场怎样的温暖之旅? 然而这些都没有。
这种冲击是直接的,就像你本来期待的是农家菜,突然上来了一桌法式大餐。
虽然预期落空,却也别有趣味。
走进第一个展厅,南京的城市元素扑面而来,六朝古都兴衰,千年文化脉络起伏。
历史学家用史笔描摹人物生平,小说家用想象场景呈现历史细节,诗人则发内心之幽情,那么声音又能做什么呢?展方选择了四段声音:魏晋古语朗诵的梁武帝萧衍《河中之水歌》、宋时古语念白的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英语诵读的《拉贝日记》片段,以及带有未来气息的科幻小说《我们生活在南京》的电波声。
四段声音都与南京有关,从古代到未来,声音背后是有景象的,闻声如见景,听音如在场。
你好像同萧衍一起在河中游荡,好像与辛弃疾一起拍了栏杆,仿佛置身于1937年那个残酷战争场景,又好像陷入到未来的慌乱未明状态之中。
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能够活化历史时期人们说话的方式,但这并不是最令人惊奇的,最让我感动的是未来的那段声音,嘈杂的无线电湮没了人声,让人有一种置身于赛博空间的感觉。
未来,声音或许会回归到一种纯粹的波的形式,带有确切含义的语言则会退居其次,甚至消失。
与四个听筒相对的是窦平平的《檐下耳语》装置,她企图以声音的形式转化文学内容,当你坐下去的时候,文学在你耳边低语,当你离开,声音随之消失。
这像是一个隐喻,有些声音,只有去听才能听到,就像我们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我们也永远无法对那些不想听我们说话的人说些什么。
沿着长长的走廊深入,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声音装置:红色帷幔之中是波浪一般起伏的钢丝结构物,其灵感来源于藏族的经幡。
古老的藏族文化,背后隐藏着关于 抚平心灵的秘密方式,装置恰 好构建了一个冥想和聚集的场所,其下方是一片镜面,象征着水。
水是平和的,水是随物赋形的,它将这种哲学韵味推向了极致。
进入装置内部,风声水声交错着人声,内部的铜铃亦随之摇曳,人因此而进入梵境。
延续这种梵境的是OPEN建筑事务所的《山谷音乐厅》的声音作品。
作品位于一个暗房之中,当我拉开帷幕,小心进入,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悬崖,风景不断变化,山、石、植物、空旷的场景等在眼前变换,之后是山谷音乐厅。
它是真实存在的,位于承德的山区,以一种空灵的、仿佛天外来物的姿态存在。
舒缓的钢琴曲从视频中流出,经春历冬,山野的景致随四时不同而如走马灯一般变化。
当我坐在屏幕前,仿佛坐在了山间,屏息聆听自然的呼吸,飘雪声、风声,以及山间特有的动植物的声音,声声入耳、入心,我与这一切融为了一体。
“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
”《淮南子》如是说。
离开山谷音乐厅,穿过遮光帘,我一下子进入了“宇宙”。
一个夺目光滑的六面体建筑出现在眼前——宇宙八音盒,这是一个企图实现人与宇宙在声音层面上实时互动的乐器。
在八音 盒两边墙面张贴着屏幕,其上播放着人类探索宇宙的场景和声音——“4、3、2、
1,点火!”人是宇宙的结晶,同时人也感受着来自宇宙的讯息。
通过声音的方式,人与宇宙相互交流。
我们听到了宇宙的波声,宇宙是否也能听到我们的八音盒里传达出来的声音呢? 在“宇宙”的隔壁,依旧是用厚重的遮光帘作为隔断,暗黑的空间里一块屏幕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初看时以为是梵高的《罗纳河畔的星夜》,坐定了发现,镜头在向前缓缓移动。
在南京声音地图项目所创作的《秦淮音河24小时》里,我们随着紧贴河面的视角,身临其境般地在秦淮河里徜徉,聆听着这座城市古老而现代的声音。
城市永远在更新,古老的城墙则只是 默默矗立。
市井永远是鼎沸的,流 水的潺潺却引人入梦。
这构成了一幅当下南京城的图像,与展厅一开始的过去的南京、未来的南京,形成了呼应。
声音一直在变化,变化的主导者是人,人享受着声音的美感和形式,人赋予了声音不可思议的想象空间,人试图用声音呈现我们所在的时空。
所以走出展厅,进入另外一个长廊,看到鲁安东(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殷漪的《三声庭》展览现场会有一种文末总结的感觉。
“我听故我在”的展签,是野心,也是一种宣言。
步出展厅,余音绕梁,同时我也在思考,一场以声音为主题的展览该是怎样的? 人其实是视觉动物。
视觉所带来的感官冲击永远是最强烈的。
卢梭曾论述过,眼睛能比耳朵接纳更多的感知对象,因此对眼睛说话比对耳朵说话更有效。
所以在人类之中形成了一种“眼睛”即“正义”的文化传统,中国人也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表现在当代艺术的展览里,视觉往往多于听觉,也往往比听觉更重要。
音乐或其他声音形式只是视觉展览的一种信息要素的补充,是一种辅助手段。
有声会更好,没有也不要紧——我们常常是这种感觉。
这不就是短视频的算法推 荐吗?永远推荐我们喜欢的,最后我们便会一直生活在我们所喜欢的氛围之中。
而那些我们所不喜的,我们很少考虑它们的死活。
它们大概率的结局也会是死亡。
我们喜欢图像的,所以图像会天长地久,而声音的、文字的那些,就会慢慢退却,直至消失。
声音是脆弱的。
儒家传统中“五经”本来是指诗、书、礼、乐、易。
其中唯独《乐记》消失了,因为它是和声音相关的文字作品,一旦隔代,后人就读不懂了,便不会流传下去。
嵇康之后再无《广陵散》,也因为它是声音的形式。
其实消失的声音,何止广陵散?我们的声音一直在消亡,大到整个地区的方言乡音,小到一个街区的叫卖声音,都是如此。
我想起外婆中气十足的声音,她总是喜欢说:“怕什么?有外婆呢!”我长大了的时候,外婆已去往另一个世界,她的声音好像还在耳边,但已经慢慢模糊,以至于不复记忆。
其实很多声音都是这样。
同时声音又是具有穿透力的。
有些声音令人不适,甚至令人害怕;有些声音令人深思,有些声音令人忘我;有些声音说不出哪里好,但就是会让我们动容不已;有些声音则成为我们记忆最深处的美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回荡。
我有时候想,声音之所以会有这种穿透性,也是因为它的绵软无力,恰好能够击中我们的内心。
一场以声音为主题的展览,是需要勇气的,是必要的,也是巧妙的。
或许从一开始它就没有想过要讨好观众,在一切都需要流量的时代,它难以成为网红展,那些抱着拍摄好看照片而去的观众,必定也会铩羽而归;但那些带着聆听之愿而来的观众,一定会像我一样坐在《山谷音乐厅》的大屏面前,心归道山。
回答之前提到的那个问题:一场以声音为主题的展览该是怎样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有现成答案的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开放式问题。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有的人会把亲人的絮语放进去,有的人会把街头叫卖放进去,有的人会把流水声放进去,有的人则可能把吵架的声音放进去,有的人会展现自相矛盾的声音,有的人会用声音探索表达的尺度和空间问题……而我希望这样的声音探索,没有止境。
“万籁”之中需要每个人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
摄影/倪清蓉 在热情消退之前让我们愉快告别 城市里餐饮业重启堂食的那天,出门约友人吃饭,在出租车上经历了许久未见的堵车。
司机抱怨钱难赚和城市生活的无聊——除了吃饭、逛商场、看电影,就没什么别的娱乐项目了。
国际旅行尚不敢多想,远程出游也受限制,城市里先风靡起了精致露营。
人们热衷于寻找近郊新开发的商业露营地,在后备箱里装上按图索骥的月亮椅、天幕、户外炊具,随时准备奔赴人造“自然”——为测试新开封的新装备,在野外聚众烤肉、喝咖啡,同时不忘架起手机三脚架。
还是要怪城市娱乐生活太贫瘠。
即便是一场远途旅行,普遍而大众的方式也不过是订目的地,然后订车票、机票、酒店,一番舟车劳顿后,继续吃饭、逛景点、压马路、打卡、消费甚至露营……只是更换下俗世生活的背景幕布。
那么,一本关于“旅行”的书,要给人看些什么不一样的? “见没见过一个地方的朝霞和晚霞。
”这是作家韩松落衡量旅行的硬指标——需要在一个地方停留足够久,或者至少需要一些深度的体验,才能称之为旅行,否则只是路过。
《浪游记》的作者有三位:王恺、韩松落、尼佬。
前两位是作家、媒体人,前者多年前跑社会新闻,去了很多偏僻地采访;另一位西北人,写了很多影评、乐评和专栏文章;尼佬是给Lonely旅行指南供稿的职业旅行家。
行走各地、随笔记录是这三位的工作和习惯,来场“六手联弹”是媒体人王恺的发心,撺掇到一起,就成了这本跟一般旅行文学不 太一样的随笔集。
从读者的角度读旅行文学,若是看单 一作者预设目的、计划的行走记录,有时不免感到疲惫。
但读《浪游记》,更容易在心态上保持轻松——它的阅读体验有些OldSchool——有些像听一张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独立音乐合辑。
被其中一两篇文章惊艳到的感受,类似当年被某个乐队“一曲入魂”,像开启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
不知王恺老师策划这本合集的时候,是不是也从老唱片里获得了些灵感?1970、1980年代的人,还比较容易有些共同的影音记忆。
《浪游记》在文章编排上也很有意思:它不按时间、空间顺序组合。
篇章设计成“自在”“乡愁”“尘间”“味道”“温度”“遇见”“阅世”七个部分,这或许是传统媒体人策划组稿的思路,翻起来就像随便翻杂志。
这让读《浪游记》变成纯粹的闲读:点根香,台灯下读几篇;用脚撸着地毯上打滚的猫读个几篇;铅笔画画线,伏在案头再翻几篇。
两天,我就“浪”着翻完了。
从书店从业者半个内行的角度看,《浪游记》的纸质书做得相当考究:小32开+裸线书脊+外封的设计,内文用纸和排版的字号、字距,都考虑到了读者的阅读舒适度,小民老二的插画有种久违的野生气息,书里的横幅摄影都做成了对开跨页,又能打开铺平到180度……种种设计细节,都能看到轻盈、舒服、散淡背后的细心思。
想来也略感到遗憾,这本书所呈现的美好——纸刊、纸书、装帧、手绘摄影、认真走路……在全民数字阅读和短视频的 当下,都有些小众。
把一本关于旅行的纸书做到这份儿上,近乎于在传承手艺了。
另注意到一细节,《浪游记》的每篇文章,开篇不署作者名,这或是三位旅人面对世间风景的谦卑心——或许三位都认同这个观念:风景不是行走的背景,人对于自上古就存在的自然来说,没那么重要。
当写作者和读者的自我,都能隐遁于荒野之中,相逢纯属偶然中的偶然。
同为过客,能共一路风景,就聊上几句。
景见过了,话讲完了,也就该告别了。
结尾署名,是记录者的如是观照,像古人一句“属予作文以记之”。
“风格即一切。
”用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对写作者的评价标准来看旅行 者,也是一样的——Ta怎么走路,看些什么,体验什么,跟什么人交谈——组成Ta自己。
相信翻完整本《浪游记》的读者不会错识三位作者。
《浪游记》里的三位,身上都有可辨识特征:身怀古风、热爱荒野的西北人是韩松落;见多了生死悲欢、转向用玩心流连俗世的是王恺;特别能走路、爱喝啤酒的孤旅人就是尼佬。
三位交出的碎片记忆也各有风格:有人于童年溪水边拾得璞玉一块,深藏多年,却于离开故地之时将它扔下山坡,猜想它终将化作宇宙星辰,这是豁然;有人奔赴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因被尘世苦难触动,止步于穷街陋巷,这是悲悯;还有人徒步尼泊尔高原,一路鲜见青蔬油水,却又在离开之后,把村落的日照金山景色忘了,也忘不了旅程中最美味的豆汤饭,这是仁爱。
何为“浪游记”?精髓该在一个“浪”字。
王恺的诠释——“随心所欲,没有目的,经常走神。
”这寓意着接纳世界以本来的模式运行,接受别人的日常于自己的生活可能相悖,对不在期待之内的意外和必然保持包容。
也唯有这样,“游”才能自在。
设定了目的方位的景致,离人归乡的风景,采访路过的偏僻陌生地……若是不带分别心、不纠结于故乡他乡此处彼处,在当下所处的地方能身心合
一,周边的三公里乃至三十米就都有风景可见。
“记”则是随记,放任自己随意散漫地记下什么,让胸中块垒或快意弥散开来。
信马由缰地写,才不会被求成的欲望牵绊住。
可能放任自己去自由行走、体验的人 ◎绿川 毕竟还是少数,这也是为什么《浪游记》里写下的人和事,能让旅人有惺惺相惜之感。
你身边或许也有这样的朋友,就像书中《惊起千只白鹤》一篇提到的马格,他们并不从事什么文艺工作,他们只是不安于室,去一个地方不拍照片,也不写什么东西,甚至他们并不谈论旅行。
只有你跟他共桌吃过饭、喝到位的那些罕见时刻,才有机缘听到些惊人故事。
诚如王恺所言:“没有一次旅行,不是回到故乡。
”人们去往别处,看风景、闲逛、吃新鲜食物,和人交谈。
因为陌生景致充分调动感官,赋予自己身心合为一处的错觉,然后回到日常栖身之所,是为了能对贫瘠的日常多些耐受。
旅行总有终点,旅人总要告别,说起来人的尘世旅行,也就是在寻刺激和谋生存中来回摇摆着度过了。
印象深刻的一段,来自尼佬的伊朗旅程:他被酒店服务员(厨师)忽悠去爬5604米的达马万德——伊朗第一峰。
司机拉上去,给他两小时自由登顶时间,下山后在野外BBQ,吃鸡肉牛肉串和蘑菇串,喝伪啤酒、抽水烟,临行前那人又来推销包车去伊斯法罕,被他拒绝,写一段文字,极喜欢:“兄弟啊,我们有半天来抽水烟,已经是不错的缘分了。
一个习惯孤独的旅人,可以给陌生的路人微笑甚至眼泪,那也只是因为陌生而肆无忌惮地放空,在热情没有化作消耗之前,让我们愉快地再见吧。
”《浪游记》之于当下的意义,也就在此。
在我们囿于一地的当下,在纸上,读一些风吹过的旅程,就在热情未消退之时,我们告别。
编辑/史祎美编/巨琳责校/方立董一凡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