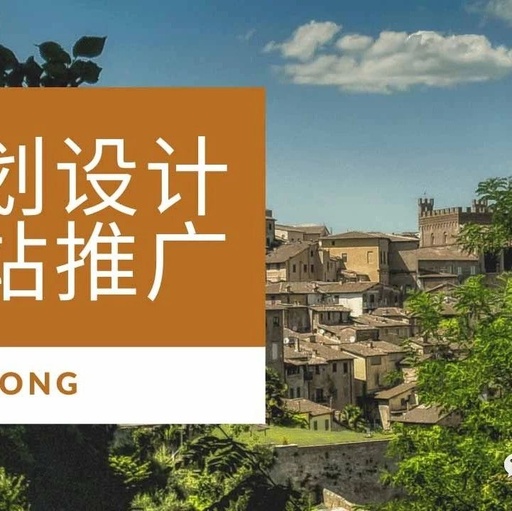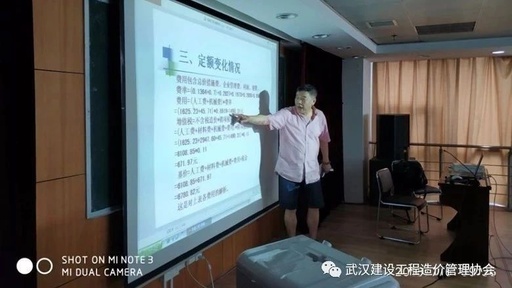年6月12日8星期
五 副刊 ANSHUNDAILY责任编辑:黄成义/校对:侯金梅/组版:张开云 三线老人 □草田
八 我的丈母娘是一个三线老人,1958年离开辽宁本溪的,再也没有回家。
那时候大跃进刚刚开始,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声中,她考上山西太原机械学校。
照片上看,当时她不到20多岁,按照当时的流行时尚,扎了长长的辫子,显得既清纯又能干。
可她今天已是80多岁,一身的腰病,天晴下雨尤其痛得厉害,是年轻时候苦干劳累过度留下的病根。
上世纪60年代初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工业体系建立的初创时期,东北以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国家的重点投入而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基地。
本来预备毕业后回东北老家,参加东北工业建设,历史的风云际会,1964年她作为支援三线建设的第一批工人来到贵州。
三线建设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战略。
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上千万人次的建设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大西南的深山峡谷、茫茫荒野,风餐露宿,肩挑背扛,付出了十几年的艰辛、血汗,甚至生命。
在时代的感召下,她来不及和家里告别,便仓促上路,这一去,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瘦弱的母亲和姐妹们没能等到她回来吃团圆饭,只得在家里为她远走他乡祝福祈祷。
梦想中的工厂是成排连片的,工人住在宿舍里,可是刚到贵阳小河,眼前的群山绵绵让他们惊呆了,没有房,是自己开山炸石头砌的房子,只有一人多高,屋顶盖牛毛毡,夏天屋里热得像蒸馒头,冬天冷得像冰窖,这种房子叫干打垒。
一到雨天,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为了接雨水,锅碗瓢盆全用上,地上完全成了和稀泥。
这样的干打垒,如果是单身,一个席棚子要挤两三人,10平方米左右的“干打垒”则要挤6个人;如果是家庭,每家不过20平方米。
理想本是技术控,毕业以后要干技术工作的,但是她老人家一辈子干后勤工作,做食堂管理员、幼儿园阿姨、招待所客房部主任,反正是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革命工作嘛,安排干啥就干啥,不讲原因,不讲条件。
1958年她从东北出来求学,当时18岁,一直到今天的80岁,这一生再没能回家,从此与家人天涯分离,惟有的只回过两次家,是结婚和母亲生了重病的时候。
丈母娘脾气很倔,工作常常主动加班,一忙就管不了两个孩子,于是就想了个办法,先喂饱孩子,然后用布带把孩子捆在床上,直到下班后回家解开。
可怜孩子饿了或者口渴就只有哭着喊着等着整整一个上午,全顾不上。
听到丈母娘骄傲地说起这些,我不知道是感动,还是不忍,总觉得那时的他们的铁石心肠,何以与现在的父母差距这么大。
011基地大院刚刚建设时,不请建筑公司,干部家属人人出力,搬水泥的搬水泥,挖土的挖土,砌砖的砌砖,不知经历了多少个白天黑夜。
那个年代工作不分男女,很多女同志抢着干男同志的活,我丈母娘也是其中之
一,今天看来也是醉了,对此,我们常常疑惑不解。
丈母娘说,她在读书时,为了赚学费,就到火车站搬水泥,一人能扛50公斤的水泥包子,所以根本不算什么。
可是,今天她老了,留下这些病根,哪里知道是当时用力过猛。
丈母娘在招待所(现在的西秀山宾馆)工作,每个星期要洗两三次床单被套,当时没有洗衣机,全靠人工洗,换下的床单被套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可她是积极分子,带着几个妇女,几个大盆,几块洗衣板,蹲下就是一天,回到家里,全身筋骨散架似的,不想动弹,更不要说吃点什么了。
后来有了洗衣机,这才解放出来。
退休后几十年,丈母娘经常喊腿麻没有知觉,腰上常年绑着护腰,可是,谈起从前的工作激情,仿佛打了强心针又激动起来。
看了王小帅的电影《闯入者》,我才知道,三线的父辈是没有自我的,说“我是谁”,他们是不敢说的,他们说得最多的往往是孙子,孩子,单位,领导,国家,社会。
今天,当年华老去,个体觉醒以后,她们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
前不久,与朋友回到废弃的老厂区,厂房出奇安静,旁边已经荒草丛生,陈旧的红砖房没人居住,环顾四周,还贴有一些标语。
我仿佛看到,人们下班回家,夕阳下山,杏红色仿佛对周围的景色染了色似的,在干打垒的公共通道,人们挤在公共水池,淘米、洗菜,有说有笑,不过,那已经是60年前的日子了。
龙岩机械厂建厂初期篮球队员留影 照片为证 □宋建英 龙飞老厂家属房 一个老职工找到我说:中航工业贵州飞机公司工会看到我在朋友圈上传的老照片非常珍贵,托她找我要几幅龙飞公司初创时期的照片,在贵飞公司创建50周年纪念活动时用。
我内心一阵感动,这感动不仅因为照片被认可,更来自于航空人对三线建设历史的敬重的共鸣。
我没有参加工厂的三线时期的创建,那时我还小。
我是随父母从北方城市来到贵州安顺这个山区小城的。
50年的贵航,50年的安顺,50年的点滴。
翻开相册时刻,内心由此而升腾起一种无限的怀想:时间可以冲淡许多记忆,但是,精神是永恒的;照片可以退去其原来的色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显得弥足珍贵。
我是1980年9月来到龙飞公司(原龙岩机械厂,代号150厂)的,并一直从事宣传工作。
30多年的宣 传工作,让我接触最多的是生产现场、生产工人,见证最多的是厂房、车间、厂容厂貌及环境的变迁和人物活动的真实场景。
也因此,我珍藏最多的便是企业各时期的历史照片,因为它是企业各个发展过程最真实的历史的见证。
在历次举办的纪念工厂周年创建活动中,我补拍、翻拍和抢拍了无数的照片。
在随后过往的日子里,每一次翻看那些珍贵的历史镜头,那里面的场景、故事以及老一辈、新一代航空人在三线地区艰苦创业的精神都会模糊我的视线。
记得在纪念龙岩厂建厂35周年活动时,我和我的同事们用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追寻龙岩三物历史足迹。
建厂纪念日那天,我们从近千幅照片中整理出105幅照片,分四个部分在厂家属区内那个长20米的阅报栏中展出。
在前言中我们写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禁不住回首过去的岁月;我们缅怀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创业的足迹;我们感怀几十年风雨兼程的日日夜夜;我们咀嚼着生活的酸甜苦辣;我们感悟着一段历史的平淡与辉煌。
这一切仿佛近在眼前,却都随时光的流逝一去不回。
可是我们发现,35年来,有一种东西是挥不去的,并始终支撑着我们鼓舞着我们前行。
它,就是我们的厂魂——自强不息。
记得当时宣传长廊纪念照片的影响非常好,有许多许多的人到宣传部索要照片留作纪念,更有很多展出的照片被老职工悄悄揭下来珍藏。
今天,我又一次翻开老照片,也翻开了龙岩厂新旧对比的变迁,翻开了浓厚的感情和深深的怀念,以此表达对龙岩三代人为中国航空工业作出贡献的敬意和对龙飞公司的创建、对中国三线建设的纪念。
诗窗 我是三线二代人 □齐乃波 无论走到哪,我都说我是贵州安顺人。
事实上,我是三线二代人,是在《突破乌江》的竹海梦幻中来到贵州,是在《铁路修到苗家寨》的悠扬歌声中来到安顺。
来贵州时,我9岁。
那年是与三线建设的父母一起乔迁到的贵州的。
一路的惊讶不说,只是进入贵州那由两个庞大的火车头吭哧吭哧的牵动,就令我终身难忘,以后就再也没见到这种阵势。
下火车是在安顺,安顺站很小,又是晚上,没有现今的出租车和大巴、中巴,更没有穿梭在站前的住宿拉客的,一切静寂得几乎让人恐怖,加上远处不时传来的“文革”武斗的枪声,没有谁敢走出火车站,好在火车站里有解放军。
解放军就是解放军,时代不同,但对群众的行为始终未变,他们把自己住宿和办公的地方让给我们休息。
第二天天亮,011基地用汽车把我们送到安顺城里的各旅社、饭店、招待所。
我家被安顿在五星旅社,因为三线企业还在建设中,我们只能暂时在城里安顿。
那一天,走进安顺城,当时城不大,从现在的新大十字到北门,由西街口到地区医院,全城走完也没有交通车,大十字那也不大,城内有广播。
幸亏有广播,因为当天广播里有个重大新闻,所以这一天的时间就牢牢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那个重大新闻就是中国“同志加兄弟”的朋友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逝世。
后来查询,胡志明逝世的日子是1969年的9月3日。
五星旅社在安顺东街小十字附近,旅社的格局是典型的老安顺居民住宅,中间有个小院坝,四周就是木制板的小二楼。
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大家就在小院坝里闲坐闲聊,都是“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走到一起”,天南海北的“好人好马”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我家还认了个干亲戚,现在还有来往呢。
住五星旅社的时间有多长,我不知道了。
但那一段的时间还是有趣的,女人们在一起就喜欢逗小孩玩,让某某女孩给谁当儿媳妇,那女孩就开始给“老婆婆”家扫地去了。
当然,我也有一个被“编排”的“媳妇”,我很生气,可她不生气,就知道和“老婆婆”拉近乎,全不管我的态度如何。
平常我们是不出五星旅社的门,若出去也是由哥哥领着,哥哥比我大三岁,领着我逛小城玩。
城里小吃多又好 吃,几毛钱就可吃到现今七八块钱才能吃到的东西。
可钱少不敢破费,看看也就知足了。
小城对我们的诱惑不仅是吃,还有好玩的,除了一分钱看小人书,好多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如何玩,而这些都以摆地摊的方式吸引我们,让我们迈不动步。
特别是到了赶场天,各种少数民族服饰的男男女女像演戏般好看,不像现在只有重大节庆和会议时才能看到盛装的少数民族。
当然,那时我也把屯堡人当成了少数民族了。
在城里居住的日子并不觉得有什么留恋的地方,那时是急盼着进厂。
看到一家家人走了,那心里不是滋味。
因为离开五星旅社不是整齐划一的,也只能说是陆陆续续的,听说是有居住条件了,干部先进厂,父母是工人,自然落到最后离开。
进厂后才知道,工厂不如城里,先进工厂不过是先吃苦。
现今想起来,由衷地钦佩那年代的干部真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三线企业的厂址大都是选择靠山隐蔽分散的地方,为此要现修通公路,现架线通电,现铺管道通水,现盖房子居住,更早一点的创业者,不夸张地说,真是天当房地当床,好一点的是搭个席棚子住下或到村寨借宿。
进厂后,进城的机会也就不多了。
一次是大舅来,他领着我们哥俩在安顺城里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把口琴;另一次是小姨嫁过来,我和家里人到火车站接她。
而真正意义进城,那是七年以后,我和同学们送朋友当兵,我不慎还丢了五块钱,很不是滋味。
那年是1976年。
那时进城虽然可以自由了,可上一次安顺,先是两毛后是四毛钱的公交车,怎么都舍不得坐。
一般都是搭便车进城,要不就和同学走路进城。
反正没有一次是车来车去的,走路一般在两个小时左右,走小路也得一个半小时。
那时城里的诱惑是电影院,当时有三家电影院,要想看到最新电影,就要进小城。
上安顺成了我们心仪的奢望。
长住安顺。
今生今世与安顺的结缘是我没有想到的,三线企业子弟的出路大都还是在三线企业,所以有“献了青春献终生,献完终生献子孙”之说。
事实上,在我们那个年代,能够进三线企业不亚于今天能当公务员。
建设·眷念 □文龙生 一年前刚过完春节,是安顺传统的“跳花节”,北门外的跳花坡,人头攒动,甚是热闹,跳花的、看跳花的、卖东西的,黑压压一大片。
一小吃摊点,几个头发花白的人,凉粉吃得正香。
跳花坡赶热闹的绝大多数是青年人,连中年人都不多,这几个“花白头发”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哎,当记者就是这样好奇。
一来二去的搭讪,原来这几个人是“老三线”,上世纪六十年代随建工三局来到安顺,支援三线建设,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随单位迁至武汉。
如今退休,适逢“三线建设”五十周年,他们结伴来安顺这个第二故乡走一走、看一看,怀念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让人感慨的是,这几位“老三线”当年工作地点在西门外野狗洞,那是建工三局的一个基层单位,距黄果树就那么二三十公里,但十多年从未去过,这次到安顺还要了却一个心愿:游览黄果树风景区,亲眼目睹大瀑布。
安顺开始三线建设的时候,我在读小学,感觉安顺突然冒出不少讲普通话的外地人,还有那从未见过的大型运载车来来往往,记得有一辆绿色大型翻斗车,压塌了北街的一处沥青路,几乎倒靠居民房。
以后才知道,这些外地人和大型车辆是建工三局(建工部第三工程局)等重点建设单位的,他们是三线建设的先驱者。
虹山轴承厂、011系统等建三线的人马,也一拨又一拨从祖国四面八方,汇集黔中大地。
国家战略转移,重视三线建设,那时有句口号“好人好马上三线”,许许多多的优秀工程师、技术员、工人等,无怨无悔从大城市来到西部山区。
他们一腔热血,胸怀大志,憧憬未来,要在三线建设战场上大显身手建功立业。
难能可贵的是,三线建设者们带来耳目一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给封闭的大山深处吹进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春风。
安顺上上下下非常支持三线建设,当时全国正处在经济困难、物资匮乏年代,安顺这样的贫困山区生活条件不言而喻,但地方政府竭尽全力,为三线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和服务。
1965年,我的幺叔和好几个商业系统同事,抽调到安顺飞机场的商业供应店,这是商业局为三线建设服务的一个专卖店,安顺许多最紧俏的、难以买到的商品,如白酒、白糖、布料,尤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这个供应店却有保障。
安顺东关设一副食品专卖店,专门供应虹山轴承厂等三线建设者。
据说当初那店是“以话取人”,讲普通话的无须票证即可购买少些猪肉,有当地人“李鬼装李逵”去买,见上秤的肉有些骨头,心里一急,吐出“家乡话”露了馅。
那时候找工作很难,要进三线建设国字号单位,更是难上加难,除了一般的“准入条件”外,还要上查三代,看家庭成分过不过硬。
所以,能在“0三七九”(011系统、建工三局、七砂、九化)工作,一人有幸,全家高兴,光宗耀祖!我小时候常听大人们唠叨“:你看,某某家孩子多有出息,在011上班啦。
”在这些单位工作,逢年过节回家探亲,亲朋好友都要来嘘寒问暖,羡慕不已。
三线建设多在深山野地,建设者们克服各种困难,默默无闻为国家作奉献,有的还一代接着一代干,真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完终生献子孙”。
有的人虽离开安顺,仍然视安顺为第二故乡,眷念着这片神奇的热土。
2006年,我到北京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培训班学习,报名注册的时候,有个学员听我来自贵州安顺,亲热得有如他乡遇故知,兴奋不已地说,他是建工三局子弟,从小在安顺长大,还在安顺三小、安顺一中读过书,对安顺最有感情,很想有一天故地重游,看看安顺的美丽风光、发展变化。
我从他递给的名片,知道他是《车友报》社长。
守望 □彤峰 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实文献系列片《龙腾东方》有一组镜头:一位瘫痪在床上的老人在用望远镜观看窗外,他久久地凝视着窗外的蓝天…… 这个老人就是三线建设时期因工致残40多年的中航工业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公司的一位老三线航空人刘培仁。
在安吉航空精密铸造公司,没有多少人认识他,只有上世纪70年代初参加三线建设的几个老职工知道他,再就是公司领导和离退办的人知道他。
然而,中航工业贵航集团公司领导没有忘记他,一直关心他,逢年过节去看望他。
中航工业党组书记、董事长林左鸣也知道他、关心他,在多次会议上提到他:“我听说安吉厂有一个老同志,建厂的时候不幸从高处摔下,结果就终身卧床。
但是,这个老同志毫无怨言。
我听了非常感动,实际上他是一个缩影,是我们贵航人、是我们贵州这批从全国各地为了建设大三线聚集而来的航空人的一个缩影,是一种精神的体现。
” 1966年9月,刘培仁响应国家号召,从沈阳黎明支援贵州三线建设,成为贵航集团安吉铸造厂建厂初期的一名创业者。
他把满腔的激情用在工厂的建设上,工作中加班加点,登高爬下,不辞劳苦。
1971年5月18日下午4时10分,44岁的刘培仁在基建工作现场装木制屋架棱条时,不幸从6米高处坠地,导致外伤性高位截瘫,从此卧床不起长达42年。
在这漫长的42年的岁月里,刘培仁没有抱怨,他始终不变的是对祖国三线建设的挂念,对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关心。
与他交谈,你会发现他没有隔世之感,天下大事、身边小事他都关心,工厂的情况他也知道不少。
躺在床上的他仍然乐观向上,忆往昔,不言苦和累,看未来,不言忧和愁。
42年来,每天吃、喝、拉、撒、睡,他都没有离开过床。
他的生活内容就是看,看书、看报、看电视,看人、看景、看窗外。
致残后,刘培仁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听听收音机来解解闷。
通过收音机,他又有了学习的劲头,从中了解国家的大事、方针政策,而厂里的广播他也天天坚持听,知晓工厂的生产发展情况。
看电视是他生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工厂自办节目,他是每期必看。
从中,他了解了工厂的形势,工厂的发展变化,了解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走向。
他说“:我是航空工业的一名守望者,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乐趣。
”一次新调来的厂领导到他家慰问,他一下就把这位领导认出来了。
这位领导感到惊奇,刘培仁笑着说“:我在厂电视新闻中看过你讲话。
” 在刘培仁的床边,除了他读书、读报用的放大镜以外,还有一架望远镜。
这是子女们专门给他买来的,让他能清楚地看到上下班的安吉职工,看悠闲散步或活动娱乐的安吉人。
当他听见窗外那熟悉的飞机轰鸣飞过的声音时,他总是举起望远镜搜索,偶尔看到蓝蓝的天空上飞过的飞机,他会情不自禁地激动一番,感受着三线人的发展进步,感受着航空人的报国情怀。
●本报地址: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葡华欧洲城●邮编:561000●办公室:0851-38118990编辑部:0851-38129899
五 副刊 ANSHUNDAILY责任编辑:黄成义/校对:侯金梅/组版:张开云 三线老人 □草田
八 我的丈母娘是一个三线老人,1958年离开辽宁本溪的,再也没有回家。
那时候大跃进刚刚开始,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声中,她考上山西太原机械学校。
照片上看,当时她不到20多岁,按照当时的流行时尚,扎了长长的辫子,显得既清纯又能干。
可她今天已是80多岁,一身的腰病,天晴下雨尤其痛得厉害,是年轻时候苦干劳累过度留下的病根。
上世纪60年代初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工业体系建立的初创时期,东北以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国家的重点投入而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基地。
本来预备毕业后回东北老家,参加东北工业建设,历史的风云际会,1964年她作为支援三线建设的第一批工人来到贵州。
三线建设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战略。
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上千万人次的建设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大西南的深山峡谷、茫茫荒野,风餐露宿,肩挑背扛,付出了十几年的艰辛、血汗,甚至生命。
在时代的感召下,她来不及和家里告别,便仓促上路,这一去,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瘦弱的母亲和姐妹们没能等到她回来吃团圆饭,只得在家里为她远走他乡祝福祈祷。
梦想中的工厂是成排连片的,工人住在宿舍里,可是刚到贵阳小河,眼前的群山绵绵让他们惊呆了,没有房,是自己开山炸石头砌的房子,只有一人多高,屋顶盖牛毛毡,夏天屋里热得像蒸馒头,冬天冷得像冰窖,这种房子叫干打垒。
一到雨天,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为了接雨水,锅碗瓢盆全用上,地上完全成了和稀泥。
这样的干打垒,如果是单身,一个席棚子要挤两三人,10平方米左右的“干打垒”则要挤6个人;如果是家庭,每家不过20平方米。
理想本是技术控,毕业以后要干技术工作的,但是她老人家一辈子干后勤工作,做食堂管理员、幼儿园阿姨、招待所客房部主任,反正是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革命工作嘛,安排干啥就干啥,不讲原因,不讲条件。
1958年她从东北出来求学,当时18岁,一直到今天的80岁,这一生再没能回家,从此与家人天涯分离,惟有的只回过两次家,是结婚和母亲生了重病的时候。
丈母娘脾气很倔,工作常常主动加班,一忙就管不了两个孩子,于是就想了个办法,先喂饱孩子,然后用布带把孩子捆在床上,直到下班后回家解开。
可怜孩子饿了或者口渴就只有哭着喊着等着整整一个上午,全顾不上。
听到丈母娘骄傲地说起这些,我不知道是感动,还是不忍,总觉得那时的他们的铁石心肠,何以与现在的父母差距这么大。
011基地大院刚刚建设时,不请建筑公司,干部家属人人出力,搬水泥的搬水泥,挖土的挖土,砌砖的砌砖,不知经历了多少个白天黑夜。
那个年代工作不分男女,很多女同志抢着干男同志的活,我丈母娘也是其中之
一,今天看来也是醉了,对此,我们常常疑惑不解。
丈母娘说,她在读书时,为了赚学费,就到火车站搬水泥,一人能扛50公斤的水泥包子,所以根本不算什么。
可是,今天她老了,留下这些病根,哪里知道是当时用力过猛。
丈母娘在招待所(现在的西秀山宾馆)工作,每个星期要洗两三次床单被套,当时没有洗衣机,全靠人工洗,换下的床单被套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可她是积极分子,带着几个妇女,几个大盆,几块洗衣板,蹲下就是一天,回到家里,全身筋骨散架似的,不想动弹,更不要说吃点什么了。
后来有了洗衣机,这才解放出来。
退休后几十年,丈母娘经常喊腿麻没有知觉,腰上常年绑着护腰,可是,谈起从前的工作激情,仿佛打了强心针又激动起来。
看了王小帅的电影《闯入者》,我才知道,三线的父辈是没有自我的,说“我是谁”,他们是不敢说的,他们说得最多的往往是孙子,孩子,单位,领导,国家,社会。
今天,当年华老去,个体觉醒以后,她们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
前不久,与朋友回到废弃的老厂区,厂房出奇安静,旁边已经荒草丛生,陈旧的红砖房没人居住,环顾四周,还贴有一些标语。
我仿佛看到,人们下班回家,夕阳下山,杏红色仿佛对周围的景色染了色似的,在干打垒的公共通道,人们挤在公共水池,淘米、洗菜,有说有笑,不过,那已经是60年前的日子了。
龙岩机械厂建厂初期篮球队员留影 照片为证 □宋建英 龙飞老厂家属房 一个老职工找到我说:中航工业贵州飞机公司工会看到我在朋友圈上传的老照片非常珍贵,托她找我要几幅龙飞公司初创时期的照片,在贵飞公司创建50周年纪念活动时用。
我内心一阵感动,这感动不仅因为照片被认可,更来自于航空人对三线建设历史的敬重的共鸣。
我没有参加工厂的三线时期的创建,那时我还小。
我是随父母从北方城市来到贵州安顺这个山区小城的。
50年的贵航,50年的安顺,50年的点滴。
翻开相册时刻,内心由此而升腾起一种无限的怀想:时间可以冲淡许多记忆,但是,精神是永恒的;照片可以退去其原来的色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显得弥足珍贵。
我是1980年9月来到龙飞公司(原龙岩机械厂,代号150厂)的,并一直从事宣传工作。
30多年的宣 传工作,让我接触最多的是生产现场、生产工人,见证最多的是厂房、车间、厂容厂貌及环境的变迁和人物活动的真实场景。
也因此,我珍藏最多的便是企业各时期的历史照片,因为它是企业各个发展过程最真实的历史的见证。
在历次举办的纪念工厂周年创建活动中,我补拍、翻拍和抢拍了无数的照片。
在随后过往的日子里,每一次翻看那些珍贵的历史镜头,那里面的场景、故事以及老一辈、新一代航空人在三线地区艰苦创业的精神都会模糊我的视线。
记得在纪念龙岩厂建厂35周年活动时,我和我的同事们用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追寻龙岩三物历史足迹。
建厂纪念日那天,我们从近千幅照片中整理出105幅照片,分四个部分在厂家属区内那个长20米的阅报栏中展出。
在前言中我们写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禁不住回首过去的岁月;我们缅怀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创业的足迹;我们感怀几十年风雨兼程的日日夜夜;我们咀嚼着生活的酸甜苦辣;我们感悟着一段历史的平淡与辉煌。
这一切仿佛近在眼前,却都随时光的流逝一去不回。
可是我们发现,35年来,有一种东西是挥不去的,并始终支撑着我们鼓舞着我们前行。
它,就是我们的厂魂——自强不息。
记得当时宣传长廊纪念照片的影响非常好,有许多许多的人到宣传部索要照片留作纪念,更有很多展出的照片被老职工悄悄揭下来珍藏。
今天,我又一次翻开老照片,也翻开了龙岩厂新旧对比的变迁,翻开了浓厚的感情和深深的怀念,以此表达对龙岩三代人为中国航空工业作出贡献的敬意和对龙飞公司的创建、对中国三线建设的纪念。
诗窗 我是三线二代人 □齐乃波 无论走到哪,我都说我是贵州安顺人。
事实上,我是三线二代人,是在《突破乌江》的竹海梦幻中来到贵州,是在《铁路修到苗家寨》的悠扬歌声中来到安顺。
来贵州时,我9岁。
那年是与三线建设的父母一起乔迁到的贵州的。
一路的惊讶不说,只是进入贵州那由两个庞大的火车头吭哧吭哧的牵动,就令我终身难忘,以后就再也没见到这种阵势。
下火车是在安顺,安顺站很小,又是晚上,没有现今的出租车和大巴、中巴,更没有穿梭在站前的住宿拉客的,一切静寂得几乎让人恐怖,加上远处不时传来的“文革”武斗的枪声,没有谁敢走出火车站,好在火车站里有解放军。
解放军就是解放军,时代不同,但对群众的行为始终未变,他们把自己住宿和办公的地方让给我们休息。
第二天天亮,011基地用汽车把我们送到安顺城里的各旅社、饭店、招待所。
我家被安顿在五星旅社,因为三线企业还在建设中,我们只能暂时在城里安顿。
那一天,走进安顺城,当时城不大,从现在的新大十字到北门,由西街口到地区医院,全城走完也没有交通车,大十字那也不大,城内有广播。
幸亏有广播,因为当天广播里有个重大新闻,所以这一天的时间就牢牢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那个重大新闻就是中国“同志加兄弟”的朋友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逝世。
后来查询,胡志明逝世的日子是1969年的9月3日。
五星旅社在安顺东街小十字附近,旅社的格局是典型的老安顺居民住宅,中间有个小院坝,四周就是木制板的小二楼。
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大家就在小院坝里闲坐闲聊,都是“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走到一起”,天南海北的“好人好马”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我家还认了个干亲戚,现在还有来往呢。
住五星旅社的时间有多长,我不知道了。
但那一段的时间还是有趣的,女人们在一起就喜欢逗小孩玩,让某某女孩给谁当儿媳妇,那女孩就开始给“老婆婆”家扫地去了。
当然,我也有一个被“编排”的“媳妇”,我很生气,可她不生气,就知道和“老婆婆”拉近乎,全不管我的态度如何。
平常我们是不出五星旅社的门,若出去也是由哥哥领着,哥哥比我大三岁,领着我逛小城玩。
城里小吃多又好 吃,几毛钱就可吃到现今七八块钱才能吃到的东西。
可钱少不敢破费,看看也就知足了。
小城对我们的诱惑不仅是吃,还有好玩的,除了一分钱看小人书,好多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如何玩,而这些都以摆地摊的方式吸引我们,让我们迈不动步。
特别是到了赶场天,各种少数民族服饰的男男女女像演戏般好看,不像现在只有重大节庆和会议时才能看到盛装的少数民族。
当然,那时我也把屯堡人当成了少数民族了。
在城里居住的日子并不觉得有什么留恋的地方,那时是急盼着进厂。
看到一家家人走了,那心里不是滋味。
因为离开五星旅社不是整齐划一的,也只能说是陆陆续续的,听说是有居住条件了,干部先进厂,父母是工人,自然落到最后离开。
进厂后才知道,工厂不如城里,先进工厂不过是先吃苦。
现今想起来,由衷地钦佩那年代的干部真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三线企业的厂址大都是选择靠山隐蔽分散的地方,为此要现修通公路,现架线通电,现铺管道通水,现盖房子居住,更早一点的创业者,不夸张地说,真是天当房地当床,好一点的是搭个席棚子住下或到村寨借宿。
进厂后,进城的机会也就不多了。
一次是大舅来,他领着我们哥俩在安顺城里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把口琴;另一次是小姨嫁过来,我和家里人到火车站接她。
而真正意义进城,那是七年以后,我和同学们送朋友当兵,我不慎还丢了五块钱,很不是滋味。
那年是1976年。
那时进城虽然可以自由了,可上一次安顺,先是两毛后是四毛钱的公交车,怎么都舍不得坐。
一般都是搭便车进城,要不就和同学走路进城。
反正没有一次是车来车去的,走路一般在两个小时左右,走小路也得一个半小时。
那时城里的诱惑是电影院,当时有三家电影院,要想看到最新电影,就要进小城。
上安顺成了我们心仪的奢望。
长住安顺。
今生今世与安顺的结缘是我没有想到的,三线企业子弟的出路大都还是在三线企业,所以有“献了青春献终生,献完终生献子孙”之说。
事实上,在我们那个年代,能够进三线企业不亚于今天能当公务员。
建设·眷念 □文龙生 一年前刚过完春节,是安顺传统的“跳花节”,北门外的跳花坡,人头攒动,甚是热闹,跳花的、看跳花的、卖东西的,黑压压一大片。
一小吃摊点,几个头发花白的人,凉粉吃得正香。
跳花坡赶热闹的绝大多数是青年人,连中年人都不多,这几个“花白头发”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哎,当记者就是这样好奇。
一来二去的搭讪,原来这几个人是“老三线”,上世纪六十年代随建工三局来到安顺,支援三线建设,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随单位迁至武汉。
如今退休,适逢“三线建设”五十周年,他们结伴来安顺这个第二故乡走一走、看一看,怀念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让人感慨的是,这几位“老三线”当年工作地点在西门外野狗洞,那是建工三局的一个基层单位,距黄果树就那么二三十公里,但十多年从未去过,这次到安顺还要了却一个心愿:游览黄果树风景区,亲眼目睹大瀑布。
安顺开始三线建设的时候,我在读小学,感觉安顺突然冒出不少讲普通话的外地人,还有那从未见过的大型运载车来来往往,记得有一辆绿色大型翻斗车,压塌了北街的一处沥青路,几乎倒靠居民房。
以后才知道,这些外地人和大型车辆是建工三局(建工部第三工程局)等重点建设单位的,他们是三线建设的先驱者。
虹山轴承厂、011系统等建三线的人马,也一拨又一拨从祖国四面八方,汇集黔中大地。
国家战略转移,重视三线建设,那时有句口号“好人好马上三线”,许许多多的优秀工程师、技术员、工人等,无怨无悔从大城市来到西部山区。
他们一腔热血,胸怀大志,憧憬未来,要在三线建设战场上大显身手建功立业。
难能可贵的是,三线建设者们带来耳目一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给封闭的大山深处吹进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春风。
安顺上上下下非常支持三线建设,当时全国正处在经济困难、物资匮乏年代,安顺这样的贫困山区生活条件不言而喻,但地方政府竭尽全力,为三线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和服务。
1965年,我的幺叔和好几个商业系统同事,抽调到安顺飞机场的商业供应店,这是商业局为三线建设服务的一个专卖店,安顺许多最紧俏的、难以买到的商品,如白酒、白糖、布料,尤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这个供应店却有保障。
安顺东关设一副食品专卖店,专门供应虹山轴承厂等三线建设者。
据说当初那店是“以话取人”,讲普通话的无须票证即可购买少些猪肉,有当地人“李鬼装李逵”去买,见上秤的肉有些骨头,心里一急,吐出“家乡话”露了馅。
那时候找工作很难,要进三线建设国字号单位,更是难上加难,除了一般的“准入条件”外,还要上查三代,看家庭成分过不过硬。
所以,能在“0三七九”(011系统、建工三局、七砂、九化)工作,一人有幸,全家高兴,光宗耀祖!我小时候常听大人们唠叨“:你看,某某家孩子多有出息,在011上班啦。
”在这些单位工作,逢年过节回家探亲,亲朋好友都要来嘘寒问暖,羡慕不已。
三线建设多在深山野地,建设者们克服各种困难,默默无闻为国家作奉献,有的还一代接着一代干,真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完终生献子孙”。
有的人虽离开安顺,仍然视安顺为第二故乡,眷念着这片神奇的热土。
2006年,我到北京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培训班学习,报名注册的时候,有个学员听我来自贵州安顺,亲热得有如他乡遇故知,兴奋不已地说,他是建工三局子弟,从小在安顺长大,还在安顺三小、安顺一中读过书,对安顺最有感情,很想有一天故地重游,看看安顺的美丽风光、发展变化。
我从他递给的名片,知道他是《车友报》社长。
守望 □彤峰 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实文献系列片《龙腾东方》有一组镜头:一位瘫痪在床上的老人在用望远镜观看窗外,他久久地凝视着窗外的蓝天…… 这个老人就是三线建设时期因工致残40多年的中航工业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公司的一位老三线航空人刘培仁。
在安吉航空精密铸造公司,没有多少人认识他,只有上世纪70年代初参加三线建设的几个老职工知道他,再就是公司领导和离退办的人知道他。
然而,中航工业贵航集团公司领导没有忘记他,一直关心他,逢年过节去看望他。
中航工业党组书记、董事长林左鸣也知道他、关心他,在多次会议上提到他:“我听说安吉厂有一个老同志,建厂的时候不幸从高处摔下,结果就终身卧床。
但是,这个老同志毫无怨言。
我听了非常感动,实际上他是一个缩影,是我们贵航人、是我们贵州这批从全国各地为了建设大三线聚集而来的航空人的一个缩影,是一种精神的体现。
” 1966年9月,刘培仁响应国家号召,从沈阳黎明支援贵州三线建设,成为贵航集团安吉铸造厂建厂初期的一名创业者。
他把满腔的激情用在工厂的建设上,工作中加班加点,登高爬下,不辞劳苦。
1971年5月18日下午4时10分,44岁的刘培仁在基建工作现场装木制屋架棱条时,不幸从6米高处坠地,导致外伤性高位截瘫,从此卧床不起长达42年。
在这漫长的42年的岁月里,刘培仁没有抱怨,他始终不变的是对祖国三线建设的挂念,对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关心。
与他交谈,你会发现他没有隔世之感,天下大事、身边小事他都关心,工厂的情况他也知道不少。
躺在床上的他仍然乐观向上,忆往昔,不言苦和累,看未来,不言忧和愁。
42年来,每天吃、喝、拉、撒、睡,他都没有离开过床。
他的生活内容就是看,看书、看报、看电视,看人、看景、看窗外。
致残后,刘培仁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听听收音机来解解闷。
通过收音机,他又有了学习的劲头,从中了解国家的大事、方针政策,而厂里的广播他也天天坚持听,知晓工厂的生产发展情况。
看电视是他生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工厂自办节目,他是每期必看。
从中,他了解了工厂的形势,工厂的发展变化,了解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走向。
他说“:我是航空工业的一名守望者,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乐趣。
”一次新调来的厂领导到他家慰问,他一下就把这位领导认出来了。
这位领导感到惊奇,刘培仁笑着说“:我在厂电视新闻中看过你讲话。
” 在刘培仁的床边,除了他读书、读报用的放大镜以外,还有一架望远镜。
这是子女们专门给他买来的,让他能清楚地看到上下班的安吉职工,看悠闲散步或活动娱乐的安吉人。
当他听见窗外那熟悉的飞机轰鸣飞过的声音时,他总是举起望远镜搜索,偶尔看到蓝蓝的天空上飞过的飞机,他会情不自禁地激动一番,感受着三线人的发展进步,感受着航空人的报国情怀。
●本报地址: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葡华欧洲城●邮编:561000●办公室:0851-38118990编辑部:0851-38129899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