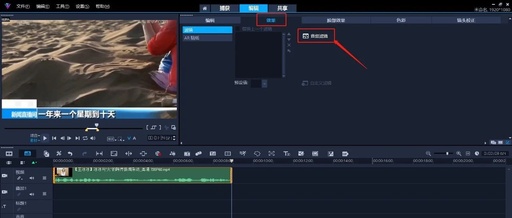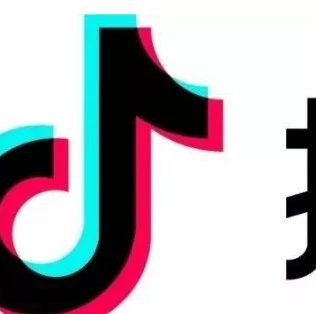12版月光城
2020年9月17日星期四责编毕璀E—mail:919370487@
知秋
包利民
一弯不知疲倦的上弦月,把角落里一只蟋蟀的琴声,钩得悠长无比。
蟋蟀的琴声唤醒了姥爷的一声叹息,在昏暗的屋子里游走不定。
窗外的黄昏还正年轻,斜阳和一串红辣椒在檐下静静地交流,从我这个角度正好可以看到它们都羞红了的脸。
檐下的燕子们最近颇为忙碌,可能正在打点行装。
走出门,南边大草甸上的蛙声渐渐涌起,却带着一种萧瑟的凉意,混合着渐黄的草叶的味道。
西边的天空中,那弯细月正驱赶着逃走的夕阳。
空气中流淌着微微的辛辣,姥爷不知什么时候走出来,衔着古老的烟斗,那一点明明灭灭的火光,正努力想点燃天上的星星。
姥爷走出院门,花狗也蔫蔫地跟着他。
扯开嗓子喊邻家的伙伴,声音越过土墙,把他家的门窗都敲红了,却也不见回应。
便觉得很没意思,想自己出去走走。
快跑几步一跃蹬上了院门前的矮墙,旁边那棵并不高大的杨树上,忽然飞起一群麻雀。
这些不安分的精灵,这时候反而越发欢快起来。
顺着土路向西,不知撞翻了多少迎面跑来的风。
走进村口高冈上那片小树林,似乎找到了风的来处,无数的风在里面嬉戏,地上薄薄一层落叶,偶尔还有被风引逗下来的,一片,两片,三片。
目光在开阔的大地上游荡,近处的一片大豆便送来阵阵起伏的铃声。
细细的河更显得清清亮亮,被奔跑的霞光踩踏得泛起层层叠叠红色的笑纹。
长长的风牵着我的衣袖,回到路口,转头间发现,姥爷正站在大坝的边缘,花狗蹲在身边。
太阳已经沉下去了,幽暗中一人一狗,像个剪影。
西边天上的那弯月更亮了,我愣怔了一会儿,猜想着姥爷在看什么,大地?落日?庄稼? 花狗发现了我,飞快地跑过来,摇动的尾巴把夜色一层层地涂抹。
我和花狗回家,姥爷依然一个人站在那儿,他手边有一点光在亮着,不知是远天醒来的星光,还是烟斗里未熄的火光。
路上遇见一辆马车,两匹马闷头走路,不紧不慢,任凭三表舅扬起的长鞭在空中绽放出一朵朵的脆响。
三表舅和路旁人家门口的人说着话,说是去镇上修理一些农具,过些日子就要用上了。
夜幕垂下来,村庄竟然比白天热闹了些。
三表舅的马车刚过去,比我大上五六岁的二歪,便驱赶着他的部队过来了。
那些绵羊还是那么脏,杂沓的足音和凌乱的喊声,把本该寂静的夜给搅乱了。
我发现,二歪已然换上了一件很厚的衣裳,上面重叠着补丁,他还是逢人就歪着头笑,有时哭着也笑。
他笑的时候,我常常忘了他是个哑巴。
想着不会再遇见牛吧?牛马羊齐全,才是真正的村庄,还有我身边的花狗。
只是一直到跳进院墙,也没看见牛。
花狗比我先一步跳进去,让我嫉妒得轻踢了它一脚,它装着哀叫了一声,把还在散步的三只鹅和七只鸭子吓了一跳。
它们跑到从窗口溜出来的灯光下,它们笨拙了许多,似乎身上的羽衣更厚实了。
那夜我睡得特别早,梦里一片繁华,五月的阳光,六月的河水,七月的大地,正把一个夏天依次绽放。
然后,或许是花狗的叫声,或许是村里其它狗的叫声,把我从梦里拽出来。
窗外,是八月的夜,西边来的风摇动着邻家园里的那几棵大杨树的枝叶,一片细细碎碎的带着凉意的声音,纷纷坠落在枕畔。
然后又睡着了,一个长长的梦,长如一生。
无数次看到大地上的种种,无数次迎着那种凉意,却没有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苍凉。
今天我生日 魏咏柏 张大伯和独生儿子住在同一个城市,去年老伴过世后,儿子叫他搬过去跟他们一起住,好歹有个照应。
张大伯没同意,觉得自己虽然退休多年,好在身体还算硬朗,洗衣做饭都难不到他,和儿子媳妇毕竟是两代人,生活习惯不一样,时间长了免不了磕磕碰碰,与其以后闹不愉快,还不如各过各的好。
于是,张大伯仍然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
平时儿子媳妇去上班,孙子去上学,张大伯从不打搅他们,只管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隔三差
五,儿子会带着老婆孩子过来看看他;遇到过节,或是儿子媳妇以及孙子生日时,张大伯也会买些礼物过去和他们一起庆祝。
今天是张大伯70岁生日,几天前他就计划好了,生日这天,等儿子打来电话,他就带着一家人去酒店摆一桌庆祝一下。
以前老伴在世时,每年一家人的生日,都是她在家里做好一桌子饭菜,然后打电话叫他们回来一起过的。
可是,从早上等到中午,张大伯都没等到儿子的电话。
今天不是周末,可能是儿子工作太忙了吧。
从中午等到晚上,儿子还是没打电话给他。
难道儿子忘了我的生日?一年就一个生日,他就我这一个老子,应该不会吧! 一直等到晚上八点多,儿子仍然没打电话给他,甚至连条短信或微信都没有。
张大伯彻底失望了,他有些气恼地拨通了儿子的电话:“你个臭小子,一天到晚忙些嘛呢?连个电话都不打!” “爸,我在家啊,您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要不要我过来一趟?”儿子在电话里焦急地问。
没良心的东西,他果然忘了我今 天生日。
“不用了,我好得很!”张大伯没好气地挂了电 话。
张大伯今天只吃了顿早餐,按说这时候早该饿 了,但和儿子通了电话后,他肚子气得胀鼓鼓的,一点也不觉得饿了。
张大伯出了门,一个人在街上沮丧地、漫无目的地溜达着。
不久,经过一家蛋糕店时,张大伯灵机一动,决定戏谑一下儿子。
他掏钱买了个蛋糕,然后拦了辆的士朝儿子家奔去。
到了儿子家,张大伯敲了敲门,开门的是大胖孙子。
见了张大伯手里的蛋糕,孙子手舞足蹈地说:“爷爷,爷爷,你怎么知道今天是贝贝的生日?” “贝贝今天生日?”张大伯被孙子拉进屋,看到贝贝脑袋上戴着寿星帽,面前小凳上放着一个精致的小蛋糕,儿子媳妇正满心欢喜、满眼怜爱地围着它。
贝贝是儿子家养的一只泰迪犬。
故园板栗香 江初昕 家乡的茶丛里长有不少板栗树,每到秋季,枝叶间藏着一个又一个浑身长刺的绒球,成双结对挂在枝头上,伴随着清爽的秋风轻盈摇曳。
那几棵粗大的板栗树,枝叶繁茂,树冠如盖,粗壮的树干要三四个人手拉着手才能合抱住,没有梯子是爬不到树上去的。
到了秋天,我们小孩子们就觑视着满树带刺的板栗。
几个同伴,以打猪草或割草的名义,慢慢靠近板栗树。
安排一个人在路口望风,到了树下,我们各自行动起来。
蹿进茶叶丛中,拿出早已藏匿好的长竹竿,对着低矮树枝上的板栗,挥舞着手中的竹竿,一阵乱扫,枝头上的板栗如下雨般的纷纷落下,同伴跳进坎沟里,全然不顾浑身是利刺的青板栗果,捡到竹篮里。
慌乱中,有四散掉落的板栗青果正好砸中树下拾板栗人的头部,“啊哟”一声惨叫,把同伴逗乐得捧腹大笑。
低矮处的板栗打完了,要想弄到高处的板栗,我们也是有办法的。
找来一尺来长的短木棍,站在高处,用劲抡起木棍朝树上丢去,木棍所到之处,枝头上的板栗“哗哗”掉下。
一番抡打之后,大家再到树下捡来短木棍,继续抡起木棍打。
几番下来,树底下满是残枝败叶和板栗青果。
有的木棍甩到树上,被挂在枝桠间,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的危险。
大伙快速捡拾完地上的板栗,躲到偏僻的地方,将带刺的外壳剥掉。
没有熟透的板栗白生生的,里面的果肉却也鲜嫩无比。
临近中秋节的时候,板栗绒球逐渐变黄,有的裂开了口子,要是夜里听到刮风,第二天,必定要起个大早,拿上书包,朝板栗树下跑去。
经过晚上 秋风一吹,不少板栗掉在地上的草丛中。
来到树底下,便俯下身子四处寻找,用木棍或用脚拨开草丛,一颗颗深褐色鼓胀的板栗就躺在草丛中。
正认真地找着,又来了几个同伴,他们也是来捡拾板栗的。
看见树下已经有人在捡了,来不及走到树下,直接从土坎上飞身跃下,霸占一块位置,这是他的地盘,赶紧趴在地上着急地找寻了起来。
东瞧瞧,西看看,生怕被人捡走了。
等把树底下都翻遍了,又抬起头来,看看满树的板栗,巴不得能掉几颗下来。
还别说,要是遇上刮风的时候,小伙伴在板栗树下捡拾板栗,会被树上落下的板栗砸中头部,大家嬉笑着说,这是正宗的“毛栗子”。
被砸中的人觉得倒霉晦气,定要把这颗栗子踩得稀烂,方能解气。
有风的日子,树下的板栗是捡拾不完的,早上捡了满满一口袋,到了晚上放学,照样可以捡到不少。
每次捡完地上的板栗,大家翻看各自的书包,见捡得多的,嬉皮笑脸伸出手来讨要一把。
也有上来就抢的,大家见状,撒腿就朝家里跑去,一路欢声笑语。
生产队里决定要打板栗了,我们小孩子们像过节一般高兴。
大人抬来长木梯,几个年轻人攀爬到树上,手持一根长长的竹篙,在树干间跳来荡去,身轻如燕,灵活似猿。
一阵狂扫之后,树下的板栗四处散落。
大人将打落下来的板栗捡拾到箩筐里,我们这些顽童则奔跑穿插于大人和树干中间,草地里、茶丛中,四处疯跑乱窜,忙得身影直扑腾。
队里打板栗的时候,小孩子是可以尽量吃的。
将板栗剥开,把玉黄色的果肉放进嘴里,轻轻一咬,那生脆、甘甜的感觉让人回味至今。
蟋蟀的琴声唤醒了姥爷的一声叹息,在昏暗的屋子里游走不定。
窗外的黄昏还正年轻,斜阳和一串红辣椒在檐下静静地交流,从我这个角度正好可以看到它们都羞红了的脸。
檐下的燕子们最近颇为忙碌,可能正在打点行装。
走出门,南边大草甸上的蛙声渐渐涌起,却带着一种萧瑟的凉意,混合着渐黄的草叶的味道。
西边的天空中,那弯细月正驱赶着逃走的夕阳。
空气中流淌着微微的辛辣,姥爷不知什么时候走出来,衔着古老的烟斗,那一点明明灭灭的火光,正努力想点燃天上的星星。
姥爷走出院门,花狗也蔫蔫地跟着他。
扯开嗓子喊邻家的伙伴,声音越过土墙,把他家的门窗都敲红了,却也不见回应。
便觉得很没意思,想自己出去走走。
快跑几步一跃蹬上了院门前的矮墙,旁边那棵并不高大的杨树上,忽然飞起一群麻雀。
这些不安分的精灵,这时候反而越发欢快起来。
顺着土路向西,不知撞翻了多少迎面跑来的风。
走进村口高冈上那片小树林,似乎找到了风的来处,无数的风在里面嬉戏,地上薄薄一层落叶,偶尔还有被风引逗下来的,一片,两片,三片。
目光在开阔的大地上游荡,近处的一片大豆便送来阵阵起伏的铃声。
细细的河更显得清清亮亮,被奔跑的霞光踩踏得泛起层层叠叠红色的笑纹。
长长的风牵着我的衣袖,回到路口,转头间发现,姥爷正站在大坝的边缘,花狗蹲在身边。
太阳已经沉下去了,幽暗中一人一狗,像个剪影。
西边天上的那弯月更亮了,我愣怔了一会儿,猜想着姥爷在看什么,大地?落日?庄稼? 花狗发现了我,飞快地跑过来,摇动的尾巴把夜色一层层地涂抹。
我和花狗回家,姥爷依然一个人站在那儿,他手边有一点光在亮着,不知是远天醒来的星光,还是烟斗里未熄的火光。
路上遇见一辆马车,两匹马闷头走路,不紧不慢,任凭三表舅扬起的长鞭在空中绽放出一朵朵的脆响。
三表舅和路旁人家门口的人说着话,说是去镇上修理一些农具,过些日子就要用上了。
夜幕垂下来,村庄竟然比白天热闹了些。
三表舅的马车刚过去,比我大上五六岁的二歪,便驱赶着他的部队过来了。
那些绵羊还是那么脏,杂沓的足音和凌乱的喊声,把本该寂静的夜给搅乱了。
我发现,二歪已然换上了一件很厚的衣裳,上面重叠着补丁,他还是逢人就歪着头笑,有时哭着也笑。
他笑的时候,我常常忘了他是个哑巴。
想着不会再遇见牛吧?牛马羊齐全,才是真正的村庄,还有我身边的花狗。
只是一直到跳进院墙,也没看见牛。
花狗比我先一步跳进去,让我嫉妒得轻踢了它一脚,它装着哀叫了一声,把还在散步的三只鹅和七只鸭子吓了一跳。
它们跑到从窗口溜出来的灯光下,它们笨拙了许多,似乎身上的羽衣更厚实了。
那夜我睡得特别早,梦里一片繁华,五月的阳光,六月的河水,七月的大地,正把一个夏天依次绽放。
然后,或许是花狗的叫声,或许是村里其它狗的叫声,把我从梦里拽出来。
窗外,是八月的夜,西边来的风摇动着邻家园里的那几棵大杨树的枝叶,一片细细碎碎的带着凉意的声音,纷纷坠落在枕畔。
然后又睡着了,一个长长的梦,长如一生。
无数次看到大地上的种种,无数次迎着那种凉意,却没有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苍凉。
今天我生日 魏咏柏 张大伯和独生儿子住在同一个城市,去年老伴过世后,儿子叫他搬过去跟他们一起住,好歹有个照应。
张大伯没同意,觉得自己虽然退休多年,好在身体还算硬朗,洗衣做饭都难不到他,和儿子媳妇毕竟是两代人,生活习惯不一样,时间长了免不了磕磕碰碰,与其以后闹不愉快,还不如各过各的好。
于是,张大伯仍然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
平时儿子媳妇去上班,孙子去上学,张大伯从不打搅他们,只管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隔三差
五,儿子会带着老婆孩子过来看看他;遇到过节,或是儿子媳妇以及孙子生日时,张大伯也会买些礼物过去和他们一起庆祝。
今天是张大伯70岁生日,几天前他就计划好了,生日这天,等儿子打来电话,他就带着一家人去酒店摆一桌庆祝一下。
以前老伴在世时,每年一家人的生日,都是她在家里做好一桌子饭菜,然后打电话叫他们回来一起过的。
可是,从早上等到中午,张大伯都没等到儿子的电话。
今天不是周末,可能是儿子工作太忙了吧。
从中午等到晚上,儿子还是没打电话给他。
难道儿子忘了我的生日?一年就一个生日,他就我这一个老子,应该不会吧! 一直等到晚上八点多,儿子仍然没打电话给他,甚至连条短信或微信都没有。
张大伯彻底失望了,他有些气恼地拨通了儿子的电话:“你个臭小子,一天到晚忙些嘛呢?连个电话都不打!” “爸,我在家啊,您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要不要我过来一趟?”儿子在电话里焦急地问。
没良心的东西,他果然忘了我今 天生日。
“不用了,我好得很!”张大伯没好气地挂了电 话。
张大伯今天只吃了顿早餐,按说这时候早该饿 了,但和儿子通了电话后,他肚子气得胀鼓鼓的,一点也不觉得饿了。
张大伯出了门,一个人在街上沮丧地、漫无目的地溜达着。
不久,经过一家蛋糕店时,张大伯灵机一动,决定戏谑一下儿子。
他掏钱买了个蛋糕,然后拦了辆的士朝儿子家奔去。
到了儿子家,张大伯敲了敲门,开门的是大胖孙子。
见了张大伯手里的蛋糕,孙子手舞足蹈地说:“爷爷,爷爷,你怎么知道今天是贝贝的生日?” “贝贝今天生日?”张大伯被孙子拉进屋,看到贝贝脑袋上戴着寿星帽,面前小凳上放着一个精致的小蛋糕,儿子媳妇正满心欢喜、满眼怜爱地围着它。
贝贝是儿子家养的一只泰迪犬。
故园板栗香 江初昕 家乡的茶丛里长有不少板栗树,每到秋季,枝叶间藏着一个又一个浑身长刺的绒球,成双结对挂在枝头上,伴随着清爽的秋风轻盈摇曳。
那几棵粗大的板栗树,枝叶繁茂,树冠如盖,粗壮的树干要三四个人手拉着手才能合抱住,没有梯子是爬不到树上去的。
到了秋天,我们小孩子们就觑视着满树带刺的板栗。
几个同伴,以打猪草或割草的名义,慢慢靠近板栗树。
安排一个人在路口望风,到了树下,我们各自行动起来。
蹿进茶叶丛中,拿出早已藏匿好的长竹竿,对着低矮树枝上的板栗,挥舞着手中的竹竿,一阵乱扫,枝头上的板栗如下雨般的纷纷落下,同伴跳进坎沟里,全然不顾浑身是利刺的青板栗果,捡到竹篮里。
慌乱中,有四散掉落的板栗青果正好砸中树下拾板栗人的头部,“啊哟”一声惨叫,把同伴逗乐得捧腹大笑。
低矮处的板栗打完了,要想弄到高处的板栗,我们也是有办法的。
找来一尺来长的短木棍,站在高处,用劲抡起木棍朝树上丢去,木棍所到之处,枝头上的板栗“哗哗”掉下。
一番抡打之后,大家再到树下捡来短木棍,继续抡起木棍打。
几番下来,树底下满是残枝败叶和板栗青果。
有的木棍甩到树上,被挂在枝桠间,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的危险。
大伙快速捡拾完地上的板栗,躲到偏僻的地方,将带刺的外壳剥掉。
没有熟透的板栗白生生的,里面的果肉却也鲜嫩无比。
临近中秋节的时候,板栗绒球逐渐变黄,有的裂开了口子,要是夜里听到刮风,第二天,必定要起个大早,拿上书包,朝板栗树下跑去。
经过晚上 秋风一吹,不少板栗掉在地上的草丛中。
来到树底下,便俯下身子四处寻找,用木棍或用脚拨开草丛,一颗颗深褐色鼓胀的板栗就躺在草丛中。
正认真地找着,又来了几个同伴,他们也是来捡拾板栗的。
看见树下已经有人在捡了,来不及走到树下,直接从土坎上飞身跃下,霸占一块位置,这是他的地盘,赶紧趴在地上着急地找寻了起来。
东瞧瞧,西看看,生怕被人捡走了。
等把树底下都翻遍了,又抬起头来,看看满树的板栗,巴不得能掉几颗下来。
还别说,要是遇上刮风的时候,小伙伴在板栗树下捡拾板栗,会被树上落下的板栗砸中头部,大家嬉笑着说,这是正宗的“毛栗子”。
被砸中的人觉得倒霉晦气,定要把这颗栗子踩得稀烂,方能解气。
有风的日子,树下的板栗是捡拾不完的,早上捡了满满一口袋,到了晚上放学,照样可以捡到不少。
每次捡完地上的板栗,大家翻看各自的书包,见捡得多的,嬉皮笑脸伸出手来讨要一把。
也有上来就抢的,大家见状,撒腿就朝家里跑去,一路欢声笑语。
生产队里决定要打板栗了,我们小孩子们像过节一般高兴。
大人抬来长木梯,几个年轻人攀爬到树上,手持一根长长的竹篙,在树干间跳来荡去,身轻如燕,灵活似猿。
一阵狂扫之后,树下的板栗四处散落。
大人将打落下来的板栗捡拾到箩筐里,我们这些顽童则奔跑穿插于大人和树干中间,草地里、茶丛中,四处疯跑乱窜,忙得身影直扑腾。
队里打板栗的时候,小孩子是可以尽量吃的。
将板栗剥开,把玉黄色的果肉放进嘴里,轻轻一咬,那生脆、甘甜的感觉让人回味至今。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