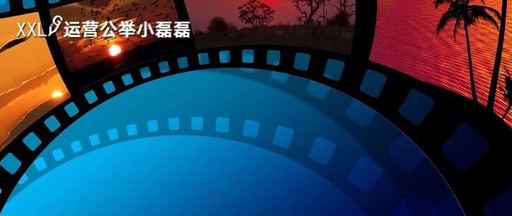美编/郑倩校对/谢永英电话/0594-2697237E-mail:abc0961@
三湾潮ANWANCHAO
春归去S□杨鹏飞
轻轻地来过,又轻轻地走了。
在桐花深处留下嫣然一笑。
随那几片薄云,飘然翻过山巅。
风吹过,一阵细雨柔柔地落进晨曦。
山那头,遥遥地传来几声鹃的叹息。
记忆里,少时的春,是家门前的一树桃花,村头池塘中的蝌蚪,上学时泥泞的小路,家后山上一眼望不到边的继木花海;是放羊时躺在硕大无比的石头上,数着山腰处传来的鹧鸪啼鸣,又几个人一伙地追逐着,从蜂声中摘一把杜鹃花瓣放进嘴里嚼着,直让羊儿惊讶地睁着眼睛,不时地瞟几下……成年后,我认识了春的名字,熟悉了春的性格喜好,便想着与春分担辛累,分享快乐。
阡陌上,与春一起种瓜种豆、割麦锄田;深山里,挑着春风春雨,百十来斤重地穿过长长的峡谷,翻过高高的山峰,听着稚笋拔节声声,以及月光下隔溪山头凄厉的狼嚎……曾多少年从政的日子里,在走村入户的风雨程中,催促着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县的春播春收进 度,比拼似地下地与老农一起扶犁,插秧……人生毕竟是由不知道多少个四季累叠的,在如春的年 华中,任何人应都不可能,仅仅只为着春而奔走。
诚然,春在我心胸里与夏秋冬一样,也只是一个角落,一幅风雨与阳光交织的,透着碧绿色的画面。
然而,四季把我的鬂须逐渐地染白了。
虽然还能够挑起六个竹箕垒叠起来的泥土担子,从冬春修水利工地上来回奔走,但必须退休了。
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唯有频繁地走进春的桃林,夏的荷亭,秋的斜阳,冬的寒山。
在心潮渐渐枯竭的时候,别样地感受到春的温和与体贴。
关注起梅花的好恶,啭莺的心情,对春的偏爱油然而生。
可当岁岁的春来春去叠加时,心底里对岁月转瞬即逝的感伤一触而发。
春尽了,冬还远吗?这是人生暮年对时光对岁月特别的感知。
不能不眷恋地数着春的每一天,又数着岁的每
一 季。
期盼梅桃的盛情而来,又担忧着桐花的悲愤而去;喜欢秋天的枫栌,却苦恼人生的白发。
望着远去的岁月背影,总想拽着春的手不放! 曾经想过,倘若春能购买,愿花尽毕生积蓄,买上五六十个春来,无须赎还年轻的面容,只需要薄田一亩梅花一树。
岁月悄悄地告诉我:春,太贵了!一个梦醒的春晨里,忽然想起,买个好心情吧,带上笔墨,到山间、到田野,也许还能画出一大片春,贴进自己心的墙壁,闲时挑几张放入微信。
晒晒其中的嫩味和露水。
转眼数载,心壁上的五颜六色,像个小春园。
心底有了春,人生的冬夏气息渐渐地淡了。
昨日,今年的春走了,可我并不觉得她真的是走了,那一片激动的梅花,还在心头豪迈着,还在心头云端里藏着。
鹃有几声叹息,然而我不! 父亲,肩挎炊盘走福州 □王雪玉 (一) “无兴不成镇,无莆不成市”。
这句莆仙俗语形容莆田人素有外出打工、经商的传统,全国各地凡是有城镇的地方,几乎都有莆仙人或其后裔辛勤耕耘的足迹。
“脚蹬草鞋,草绳捆腰,肩挎炊盘走福州”。
1953年春天,祖父与乡民九舜、亚宗等人结伴,带上自家收获的花生、蚕豆、豌豆等农作物,徒步三天三夜到达福州,租住栈房位于仓山区长安村10号,从事碗糕、米糕、软糕及贩卖农作物小生意。
1965年,父亲20岁。
祖父带上父亲到福州,教授他制作软糕及碗糕的技艺;中途因工商管理部门打击投机倒把,父子俩被迫中断小生意,返乡两年;1978年改革开放,各行各业遍地开花,一拨村民跟随父亲走福州,共同租住位于仓山区象园村一爿栈房,一直做生意到2000年冬天。
那年冬天,当地对环境卫生进行整治,栈房内用于舂米的石碓、蒸炊软糕的鼎灶器具被全部毁坏,父亲与村民无奈返乡,另谋生计。
时光斑驳了记忆,岁月沧桑了容颜。
父亲年近八旬,听他和缓讲述33年走福州艰苦谋生,一路上所历经的那些人、那些事…… (二) 每日,父亲将粳米淘洗后,放置米桶浸泡一个昼夜,次日夜幕时分,再把浸泡好的粳米倒入米筐滤掉水分,然后倒进石碓,抡起14公斤重的碓头,对准石臼里的粳米“嗵嚓、嗵嚓”舂打180锤后,进而沿着碓围,用碓头轻轻研磨成细粉、掏出,用筛笼连续6遍筛出粉末,再配白糖搅拌均匀,最后用湿水的细密白纱布盖住粉面,仅舂碓一个工序前后历时3个钟头。
软糕舂打后,次日凌晨5时许,父亲起床蒸炊。
他再次用筛笼将细粉筛至木炊桶里,接着手压圆木板,磨实粉末平面后,用薄铜片先横向割行,再纵向割行,继而搬起木炊桶,置于大鼎上方,灶膛里添加木柴,用旺火蒸炊半个钟头后,软糕熟透,炊盘底置一白纱巾,父亲拍拍木炊桶四沿,运足臂力将木桶瞬间倒扣,一朵圆实雪白的大软糕滑入炊盘,再抽出纱巾四角,覆盖在软糕上方,最后盖上炊盘盖。
父亲打理衣衫,穿上军用鞋,一身干净利落。
他撑开椅架,扣上大炊盘,挎在肩头,33年漫漫光阴,用脚步丈量福州城郊及市中心。
他肩挎炊盘进百货店、学校、食杂店、茶摊、评话馆、书店、工厂、鞋城、汤池(澡堂)等处,用一口地道的福州话叫卖“软糕、软糕……” 父亲纯手工制作的软糕,细白若雪且糯甜适中,每天下午不到4时即全部卖完。
他挎着椅架上方空空的大炊盘,心底盘算除了小本钱,当天这一盘软糕可盈利多少,乐滋滋地回到栈房,浑身是力气投入加工软糕的工序中。
(三) 每年同父亲在福州做软糕的村民大部分在夏冬两季,提前返乡避暑过年,而父亲为多挣钱补贴家用和培养3个子女上学,克服小暑炎热及隆冬寒冷,仍每日叫卖软糕舍不得停歇,将每个月积攒的现金,用信封包好,托付宗亲回乡交与母亲。
大暑一到,父亲这才打理返乡事宜。
返乡前夕,父亲到位于台江区台江路的良友茶庄,购买茉莉花茶数斤。
他说,平日家中抓猪出栏、扛猪过秤、修补蒸笼及每回托宗亲带钱回家等事,麻烦了部分乡民帮忙,福州茉莉花茶货真价廉,送一两包茉莉花茶感谢对方,理所应当。
茶香日月悠,茶中情谊长。
在父亲心里,那份乡情乡谊何其质朴珍贵啊!福州烛台,远近闻名。
乡人纷纷嘱托父亲过年回乡,帮捎买烛台,在辞年、元宵、寿诞、婚庆、乔迁等喜庆场合摆设之用。
父亲掏出本子,逐一登记各户名字及购买烛台的数量、样式及大中小。
年关前夕,父亲牢记乡民嘱托,他前往台江区一佛具店,挑选福寿、双喜或龙凤样式的合金大中小烛台,还细心叫店家一一打上票据,再将烛台分装两大麻袋,用竹杠肩挑回栈房。
每回父亲肩挑两大麻袋烛台及随身物品,搭乘公共汽车返乡。
到达家中后,乡人纷纷登门付钱取烛台,向父亲连声道谢。
一口石碓,一把碓头;舂碓声声,米香弥漫。
一把椅架,一副炊盘;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父亲,肩挎炊盘走福州的坚韧刚毅的形象,清晰如昨。
往山里,去宁里□邹易 去山里郑倩作 立夏刚过,不减春意,鹅黄、嫩绿和深黛汇成极饱和的绿色,浓烈涂抹了省道202两侧的山野,白色的油桐花星星点点写在绿色画幕上。
萩芦溪相伴而行,时而闪进视线,时而隐入绿树青山后,莹绿、碧澄,一曲蜿蜒流淌,点缀了青山,又被绿树点缀。
车在绿水青山间行进。
往山里去。
从地势上看,出涵江城区,过梧塘,自萩芦始,就已踏入山里。
道路通畅,虽海拔悄然抬高,人却并不太察觉。
从省道拐上通往宁里的路,才意识到此身已真在山里,七扭八拐的路,一个接一个的坡,二十多里的蜿蜒道路,把人逐渐引入山的胸腹。
我们到达闽中特委驻地旧址,置身庄边镇凤际村宁里。
“里”,古时为居民聚居之地。
《说文》:“里,居也。
从田,从土。
凡里之属皆从里。
”又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之说。
有人聚居,便是村落。
而“宁里”,是“使里安宁”还是“安宁的里”?不管何种,皆含美好寓意。
的确,在山坳里,山风过耳,四野寂静,没有市声嘈杂,人的话音,听起来都格外干净、清晰。
难怪鸟雀声和滴水声总是那么清脆。
可是,八十多年前,当中共闽中特委机关和闽中工农游击队根据地被迫从常太转移到庄边山溪,再到宁里,他们面对的却是穷山恶水。
这里不但山高岭峻、地势偏僻,更是山路崎岖、交通不便,而且村落分散,人烟稀少,是国民党军警不屑也不愿意踏足的。
正是这恶劣的环境,却被革命先驱们视为难得宝地。
在这里,他们发展革命,训练队伍,壮大革命力量。
在这里,他们改编部队,组织义勇军北上抗日。
在这里,他们开荒种地,建窑烧炭,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地下活动,保留革命火种。
在这里,他们举办了多期县、区干部学习班、培训班,比如“干训班“”军训班”,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 这一切,当我们站立在此地时,是看不见的,也听不见的。
由门房、大厅、后厅、天井,以及两旁几座两层楼房相互联结组成的旧址,安静站立着。
我捕捉可能的气息,寻觅也许尚存的痕迹,来告诉自己,曾经有人在这里简衣陋食、忧国忧民,曾经有战火硝烟围困和疾病、饥寒的威胁,但是山林安静、墙壁安静,天井泄下的日光安静。
我突然有些恐慌,那一段历史,将由谁讲述,用什么讲述?陈列室、教室、宿舍、广场经过重新修整,尽皆静默。
时间从不为谁停留,在我观看陈列室壁上一幅幅展板时,在我流连于红军学校教室时,在我站立沙盘 时,时间依旧不疾不徐在流逝。
时间带走了血火硝烟,带走了山岚溪水,带走了一代代人。
时间的河流在冲刷,在淘洗,会留下什么,我们又该往其中填充什么? 站在古朴的驻地旧址,我想起闽中红旗不倒精神。
仅涵江山区,就有许许多多的革命遗址。
这些地方,是时间河流上的一个个埠头,它们联结起革命发展的脉络。
1928年3月,澳柄山区诞生了闽中地区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莆田游击队,随后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23军第207团旧址在东泉圆通寺宣告成立,队伍战斗在白沙镇澳柄宫附近一带。
澳柄宫现在是红军207团旧址。
1930年,中共莆属特委成立,红军207团改编为福建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转移新县镇外坑,年底,在宣德宫成立外坑乡苏维埃政府。
但由于力量悬殊,政权被国民党军摧毁。
此后直到1936年,闽中游击队曾一度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仍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形成以常太为中心的莆仙边游击根据地。
1936年10月,中共闽中特委转移到庄边镇宁里,直到1941年离开前往永泰,留下了如今的特委驻地旧址。
大洋乡闽中革命司令部,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闽中特委从永泰迁回大洋,改为闽中地委、闽中工委。
1949年2月,闽浙赣人民游击队闽中支队司令部在大洋乡成立。
于是,有了现在的闽中革命司令部。
革命遗址遍布涵江山区五个乡镇。
在萩芦镇官林村,则有苏华故居,人们纷纷前来瞻仰,到这位为革命事业奉献青春和鲜血的革命者故里学习。
革命遗址遍布在山里。
残酷的斗争形势,迫使革命者不得不凭借恶劣的环境条件,与敌周旋。
宁里地处莆田和永泰交界处,真是山里又山里。
后来他们一路从山里走进城里。
那时起,山里、城里、这里,那里,都一片安宁。
处处皆“宁里”。
我想象,若没有车辆相助,凭双脚,走山路,可能还要负重,今天的我们,可还能走得进宁里来?对着眼前久历风雨的老房子,我发现,它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在无声注视。
驻地旧址后面,一片茂密竹林,竹子身姿挺拔,长势昂扬,让人感受到一种精神一种气势。
当初,当革命者在这里学习、训练时,是否也有一片竹林相伴? 辞别宁里,出山里,返回城里,道路从弯曲陡峭,逐渐宽广平缓。
阳光照耀着,车窗外,近水远山透着昂扬向上的气息。
石榴花(外一章) 一串串红鞭炮,遇上阳光,一点就着,把乡村小院炸得喜气洋洋,把父亲脸上皱纹炸得一平如展,把母亲炊烟炸得节节攀高,把村姑娘爱情炸得家喻户晓,喜庆的红色,为夏日乡村嫩绿肤色涂上一层淡淡的胭脂红。
石榴花开罢,摇身变成一盏小灯笼,由青慢慢变黄,悄悄用月光酝酿一坛芬芳美酒,待到农历八月十
五,大大方方地捧出献给月老中秋。
□吴晓波 我爱石榴花,更爱它爽朗泼辣的性格,大大咧咧一笑,火辣辣的目光,让所有挂在眉梢上的颓废和萎靡弯下了腰。
我爱石榴花,更爱它平实旷达的人生态度,多少次狂风暴雨后,总是绽放枝头,绚丽成五彩缤纷的笑颜。
看着石榴花,我也想站在它们中间,开成它们中的一朵,大胆热烈地张扬着生命的美好和热爱。
月季花 玫瑰虽好,却离我总有一段悠长的距离,只可远观而不可亲。
再说,玫瑰那高昂的头颅,华丽的服饰,冷艳的表情,总是让我这只癞蛤蟆望而却步,产生几分自卑。
是你,房前檐下,路边街头,风雨无阻,总是默默伴随我的左右。
清晨,你用你灿烂的笑靥,向我第一声问好;傍晚,你用你挂在嘴角上的调皮,向我道一声珍重。
一朵朵月季花,像常年在家操持家务的妻子,可能有点土气,可能有点小脾气,可能有点唠叨,可又是那么真实美丽,摸得着一颗质朴而敦厚的心。
看着月季花,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那枝上最红的一朵,就是我那朴实贤惠的妻,今后,我要倍加珍惜,好好地呵护你。
牵牛花 牵牛花是喜庆的花。
一串串牵牛花爬上藤架,把一串串火红小喇叭挂在乡村脖子上;阳光憋足了劲,鼓起腮帮子,“滴答,滴答”吹起迎亲唢呐,在布谷清脆的伴奏下,母亲搀扶稻花姑娘,披上洁白盖头,登上风的花轿,纷纷出嫁。
牵牛花是勤劳的花。
它们和乡亲们一样,栉风沐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暗合着乡村千年不变的鼓点;它们既不想像牡丹那样雍 容华贵,也不想像兰花那样骄气矫情,只想用生命的小喇叭为辛勤耕作的乡亲们加油鼓劲。
牵牛花是幸福的花。
六月的汗水轻轻一浇,牵牛花就开了,一颗火红的心,给季节染上红彤彤的底色,父亲站在底色之上,挥舞银色镰刀,敲开一扇丰收大门。
每年入夏,牵牛花都会在我记忆河流里鲜活,笑盈盈地伸出手,引着我走进一个热火朝天、汗流浃背的夏。
MEIZHOUDAILY 2022年5月16日星期
一 书店 □方宝璋 我极少逛街,但如果逛街,一般去处就两个地方,其中之一就是逛书店。
记得在福建师大任教时,所住康山里宿舍区旁边有家晓风书店。
书店刚开张时,规模较大,面积有两百多平方米。
更令人感到惬意的是书店专卖高雅、学术性强的图书,如近代文化名人陈寅恪、胡适、吴宓等的传记,二十四史、世界学术名著译丛等。
书店的装修也很雅致,墙上挂着一对硕大的牛角、几幅字画,书店中间摆着几张靠背椅、茶几,不时还播放音量极小的西洋古典音乐。
总之,让人一跨进书店的大门,就立刻感觉到书卷气息。
由于书店紧挨着我住的宿舍区,我虽然忙,但还是不时光顾,一是看看到了什么新书,二是去享受一下温馨的书卷气息。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书店就缩小了规模,分割出一半作为服装店,书店的靠背椅、茶几等消失了。
过了一年半载,书店又缩小了规模,再分割出一半作餐饮店。
墙上的牛角、字画也消失了,四面墙壁都摆满了书架,堆着各种各样的图书,书店中间也摆着柜子,柜面上散落着琳琅满目的画册、字帖等。
整个书店只有柜子旁边两条窄窄的通道可让读者进出。
从此,我去书店的次数明显减少,因为那狭窄杂乱的空间,那闷人的气息,让人无法在店里久留。
我调到江西财大后,每年都会去莆田学院或福建税校上函授课。
两校附近,曾有两三家书店。
每当我上完课,傍晚吃饭前,就信步走到那几家书店看看。
记得第一次去逛那几家书店时,让我吃了一惊,有家席殊书店,布置虽然比不上晓风书店刚开张时的那么雅致,但也令人感觉到浓浓的书卷气息。
我惊讶在莆田那样小的城市里,竟然有这样品味的书店存在。
但是,同样好景不长,过了一两年后,我再去莆田学院上课时,发现席殊书店命运比晓风书店更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游戏机店。
自从走上治学的道路,我到了全国不少的城市。
每当我初到一座城市,总抽空上街逛一下,领略一下这座城市的风貌。
我总喜欢到这座城市的最大图书城去看看。
我觉得每座城市的图书城、书店是这座城市最直观的文化窗口。
我曾到过南方一座繁华的城市,街道上高级轿车川流不息,霓虹灯五光十色,商店里各种各样商品令人目不暇接。
但是该城最大的图书城冷冷清清,空旷的书店里只有两三个读者,书橱上摆放着《致富秘诀》《富爸爸》之类的书籍。
南方那座城市之所以书店冷冷清清,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该市虽然经济发达,但却是文化沙漠,整座城市没有一所有名的大学。
而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高校数量居全国前茅,而且又有北大、清华、人民大学等全国一流的大学,这是书店生存发展的最好环境。
对于书店与文化的关系,我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和研究。
但我感觉,或许中国书店繁荣之时,即是中国文化昌盛之日。
说墨 □李天宝 自古以来,文人就与墨结下不解的情缘。
这不,旧时农村里老人常常把有文化的人,称作肚里有“墨水”的人。
我自诩是半个文人,所以舞文弄墨是在所难免的,从这一点看,也勉强算得上一个“墨客”。
因而,我向来喜欢墨。
但要说我第一次与墨打交道,却不是起于文学,甚至不是起于书写,而是源于一种工具——墨斗。
我爷爷是个修船匠,往高大上去说,是能工巧匠鲁班门下,自然而然就有一个糊口用的鲁班工具箱。
那工具箱里,有的是刨子、锯子、斧子、尺子等。
我最喜欢的却是放在工具箱小方格里的墨斗。
之所以喜欢墨斗,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拉出墨线,能刻画下自己所想要的线条。
虽然常常因拉线时被墨汁飞溅成花猫脸而没少挨父母的骂,但我每次还是乐此不疲,等爷爷收工回家,刚放好工具箱,我就偷偷去拨弄一番。
稍大以后,墨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样充满了神奇的东西。
它不仅能用来写很漂亮的春联,还能被父母当作消炎药一样用来对付被蚊虫叮咬的包包,而最神奇的是,当有人生了一种土名“飞蛇”的皮肤病时,只要用毛笔沾墨,在墙上画一个人形,再写上“金木水火土”加一个“斩”字,就能把病治好了。
在那时的我想来,这种治病方法,不是人的功劳,而是因为墨的神奇与灵异。
大概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吧,我家刚刚盖了新房子,第一年在新居过年,按风俗,要很隆重写一厅的春联。
父母是文盲,于是,硬要我写。
父亲还连哄带骗说“:你就大胆写,以前不是有人用碗底印上去也是可以的,你写上字就行了。
”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写毛笔”的经历,也为此沾上了墨香,而没有想到,这一沾就延续了30年。
后来,每一年的写春联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的身上,为此我和墨的联系也就越发紧密起来。
我写字功底差,每每写起春联来,那字完全是野路子,但因墨的缘故,我还是常常写着写着,就会沉醉在那沁人心脾的墨香之中。
到了大学毕业,我第一次收到同学赠送的一方墨锭,心里甚为欢喜。
在此之后,我还特意对墨做了一番了解。
从而,我知道了墨一般分松烟与油烟两种,了解了古时制墨名家有五代十国时的李延硅父子,有宋徽宗赵佶,有明时程君房,有清代曹素功与胡开文等。
我后来还去古玩市场淘墨,并于2005年淘得程君房彩墨一锭,记得当时很有一番捡漏之喜,虽然后来知道那是赝品,但那过程也是不亦乐乎。
随着年岁见长,我对很多事都变得无欲无求,但对于墨的喜爱却是依旧炽热。
我还是会如之前一样,到古玩市场淘墨,因眼界与经济能力故,我常常淘回来的,都是赝品、次品,但也不气馁,还常常自我安慰说,古人云“:古墨可以当药。
”我这文学病,还真需要古墨这一剂药来医。
我后来甚至因为出于对墨的喜爱,干脆就用了粹墨木一为笔名,还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粹墨居。
说起墨来,我似乎还有很多很多话要说。
我知道,我与墨的这不解之缘是不想断了。
我希望自己能和墨定一个一世不离不弃的情缘。
在桐花深处留下嫣然一笑。
随那几片薄云,飘然翻过山巅。
风吹过,一阵细雨柔柔地落进晨曦。
山那头,遥遥地传来几声鹃的叹息。
记忆里,少时的春,是家门前的一树桃花,村头池塘中的蝌蚪,上学时泥泞的小路,家后山上一眼望不到边的继木花海;是放羊时躺在硕大无比的石头上,数着山腰处传来的鹧鸪啼鸣,又几个人一伙地追逐着,从蜂声中摘一把杜鹃花瓣放进嘴里嚼着,直让羊儿惊讶地睁着眼睛,不时地瞟几下……成年后,我认识了春的名字,熟悉了春的性格喜好,便想着与春分担辛累,分享快乐。
阡陌上,与春一起种瓜种豆、割麦锄田;深山里,挑着春风春雨,百十来斤重地穿过长长的峡谷,翻过高高的山峰,听着稚笋拔节声声,以及月光下隔溪山头凄厉的狼嚎……曾多少年从政的日子里,在走村入户的风雨程中,催促着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县的春播春收进 度,比拼似地下地与老农一起扶犁,插秧……人生毕竟是由不知道多少个四季累叠的,在如春的年 华中,任何人应都不可能,仅仅只为着春而奔走。
诚然,春在我心胸里与夏秋冬一样,也只是一个角落,一幅风雨与阳光交织的,透着碧绿色的画面。
然而,四季把我的鬂须逐渐地染白了。
虽然还能够挑起六个竹箕垒叠起来的泥土担子,从冬春修水利工地上来回奔走,但必须退休了。
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唯有频繁地走进春的桃林,夏的荷亭,秋的斜阳,冬的寒山。
在心潮渐渐枯竭的时候,别样地感受到春的温和与体贴。
关注起梅花的好恶,啭莺的心情,对春的偏爱油然而生。
可当岁岁的春来春去叠加时,心底里对岁月转瞬即逝的感伤一触而发。
春尽了,冬还远吗?这是人生暮年对时光对岁月特别的感知。
不能不眷恋地数着春的每一天,又数着岁的每
一 季。
期盼梅桃的盛情而来,又担忧着桐花的悲愤而去;喜欢秋天的枫栌,却苦恼人生的白发。
望着远去的岁月背影,总想拽着春的手不放! 曾经想过,倘若春能购买,愿花尽毕生积蓄,买上五六十个春来,无须赎还年轻的面容,只需要薄田一亩梅花一树。
岁月悄悄地告诉我:春,太贵了!一个梦醒的春晨里,忽然想起,买个好心情吧,带上笔墨,到山间、到田野,也许还能画出一大片春,贴进自己心的墙壁,闲时挑几张放入微信。
晒晒其中的嫩味和露水。
转眼数载,心壁上的五颜六色,像个小春园。
心底有了春,人生的冬夏气息渐渐地淡了。
昨日,今年的春走了,可我并不觉得她真的是走了,那一片激动的梅花,还在心头豪迈着,还在心头云端里藏着。
鹃有几声叹息,然而我不! 父亲,肩挎炊盘走福州 □王雪玉 (一) “无兴不成镇,无莆不成市”。
这句莆仙俗语形容莆田人素有外出打工、经商的传统,全国各地凡是有城镇的地方,几乎都有莆仙人或其后裔辛勤耕耘的足迹。
“脚蹬草鞋,草绳捆腰,肩挎炊盘走福州”。
1953年春天,祖父与乡民九舜、亚宗等人结伴,带上自家收获的花生、蚕豆、豌豆等农作物,徒步三天三夜到达福州,租住栈房位于仓山区长安村10号,从事碗糕、米糕、软糕及贩卖农作物小生意。
1965年,父亲20岁。
祖父带上父亲到福州,教授他制作软糕及碗糕的技艺;中途因工商管理部门打击投机倒把,父子俩被迫中断小生意,返乡两年;1978年改革开放,各行各业遍地开花,一拨村民跟随父亲走福州,共同租住位于仓山区象园村一爿栈房,一直做生意到2000年冬天。
那年冬天,当地对环境卫生进行整治,栈房内用于舂米的石碓、蒸炊软糕的鼎灶器具被全部毁坏,父亲与村民无奈返乡,另谋生计。
时光斑驳了记忆,岁月沧桑了容颜。
父亲年近八旬,听他和缓讲述33年走福州艰苦谋生,一路上所历经的那些人、那些事…… (二) 每日,父亲将粳米淘洗后,放置米桶浸泡一个昼夜,次日夜幕时分,再把浸泡好的粳米倒入米筐滤掉水分,然后倒进石碓,抡起14公斤重的碓头,对准石臼里的粳米“嗵嚓、嗵嚓”舂打180锤后,进而沿着碓围,用碓头轻轻研磨成细粉、掏出,用筛笼连续6遍筛出粉末,再配白糖搅拌均匀,最后用湿水的细密白纱布盖住粉面,仅舂碓一个工序前后历时3个钟头。
软糕舂打后,次日凌晨5时许,父亲起床蒸炊。
他再次用筛笼将细粉筛至木炊桶里,接着手压圆木板,磨实粉末平面后,用薄铜片先横向割行,再纵向割行,继而搬起木炊桶,置于大鼎上方,灶膛里添加木柴,用旺火蒸炊半个钟头后,软糕熟透,炊盘底置一白纱巾,父亲拍拍木炊桶四沿,运足臂力将木桶瞬间倒扣,一朵圆实雪白的大软糕滑入炊盘,再抽出纱巾四角,覆盖在软糕上方,最后盖上炊盘盖。
父亲打理衣衫,穿上军用鞋,一身干净利落。
他撑开椅架,扣上大炊盘,挎在肩头,33年漫漫光阴,用脚步丈量福州城郊及市中心。
他肩挎炊盘进百货店、学校、食杂店、茶摊、评话馆、书店、工厂、鞋城、汤池(澡堂)等处,用一口地道的福州话叫卖“软糕、软糕……” 父亲纯手工制作的软糕,细白若雪且糯甜适中,每天下午不到4时即全部卖完。
他挎着椅架上方空空的大炊盘,心底盘算除了小本钱,当天这一盘软糕可盈利多少,乐滋滋地回到栈房,浑身是力气投入加工软糕的工序中。
(三) 每年同父亲在福州做软糕的村民大部分在夏冬两季,提前返乡避暑过年,而父亲为多挣钱补贴家用和培养3个子女上学,克服小暑炎热及隆冬寒冷,仍每日叫卖软糕舍不得停歇,将每个月积攒的现金,用信封包好,托付宗亲回乡交与母亲。
大暑一到,父亲这才打理返乡事宜。
返乡前夕,父亲到位于台江区台江路的良友茶庄,购买茉莉花茶数斤。
他说,平日家中抓猪出栏、扛猪过秤、修补蒸笼及每回托宗亲带钱回家等事,麻烦了部分乡民帮忙,福州茉莉花茶货真价廉,送一两包茉莉花茶感谢对方,理所应当。
茶香日月悠,茶中情谊长。
在父亲心里,那份乡情乡谊何其质朴珍贵啊!福州烛台,远近闻名。
乡人纷纷嘱托父亲过年回乡,帮捎买烛台,在辞年、元宵、寿诞、婚庆、乔迁等喜庆场合摆设之用。
父亲掏出本子,逐一登记各户名字及购买烛台的数量、样式及大中小。
年关前夕,父亲牢记乡民嘱托,他前往台江区一佛具店,挑选福寿、双喜或龙凤样式的合金大中小烛台,还细心叫店家一一打上票据,再将烛台分装两大麻袋,用竹杠肩挑回栈房。
每回父亲肩挑两大麻袋烛台及随身物品,搭乘公共汽车返乡。
到达家中后,乡人纷纷登门付钱取烛台,向父亲连声道谢。
一口石碓,一把碓头;舂碓声声,米香弥漫。
一把椅架,一副炊盘;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父亲,肩挎炊盘走福州的坚韧刚毅的形象,清晰如昨。
往山里,去宁里□邹易 去山里郑倩作 立夏刚过,不减春意,鹅黄、嫩绿和深黛汇成极饱和的绿色,浓烈涂抹了省道202两侧的山野,白色的油桐花星星点点写在绿色画幕上。
萩芦溪相伴而行,时而闪进视线,时而隐入绿树青山后,莹绿、碧澄,一曲蜿蜒流淌,点缀了青山,又被绿树点缀。
车在绿水青山间行进。
往山里去。
从地势上看,出涵江城区,过梧塘,自萩芦始,就已踏入山里。
道路通畅,虽海拔悄然抬高,人却并不太察觉。
从省道拐上通往宁里的路,才意识到此身已真在山里,七扭八拐的路,一个接一个的坡,二十多里的蜿蜒道路,把人逐渐引入山的胸腹。
我们到达闽中特委驻地旧址,置身庄边镇凤际村宁里。
“里”,古时为居民聚居之地。
《说文》:“里,居也。
从田,从土。
凡里之属皆从里。
”又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之说。
有人聚居,便是村落。
而“宁里”,是“使里安宁”还是“安宁的里”?不管何种,皆含美好寓意。
的确,在山坳里,山风过耳,四野寂静,没有市声嘈杂,人的话音,听起来都格外干净、清晰。
难怪鸟雀声和滴水声总是那么清脆。
可是,八十多年前,当中共闽中特委机关和闽中工农游击队根据地被迫从常太转移到庄边山溪,再到宁里,他们面对的却是穷山恶水。
这里不但山高岭峻、地势偏僻,更是山路崎岖、交通不便,而且村落分散,人烟稀少,是国民党军警不屑也不愿意踏足的。
正是这恶劣的环境,却被革命先驱们视为难得宝地。
在这里,他们发展革命,训练队伍,壮大革命力量。
在这里,他们改编部队,组织义勇军北上抗日。
在这里,他们开荒种地,建窑烧炭,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地下活动,保留革命火种。
在这里,他们举办了多期县、区干部学习班、培训班,比如“干训班“”军训班”,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 这一切,当我们站立在此地时,是看不见的,也听不见的。
由门房、大厅、后厅、天井,以及两旁几座两层楼房相互联结组成的旧址,安静站立着。
我捕捉可能的气息,寻觅也许尚存的痕迹,来告诉自己,曾经有人在这里简衣陋食、忧国忧民,曾经有战火硝烟围困和疾病、饥寒的威胁,但是山林安静、墙壁安静,天井泄下的日光安静。
我突然有些恐慌,那一段历史,将由谁讲述,用什么讲述?陈列室、教室、宿舍、广场经过重新修整,尽皆静默。
时间从不为谁停留,在我观看陈列室壁上一幅幅展板时,在我流连于红军学校教室时,在我站立沙盘 时,时间依旧不疾不徐在流逝。
时间带走了血火硝烟,带走了山岚溪水,带走了一代代人。
时间的河流在冲刷,在淘洗,会留下什么,我们又该往其中填充什么? 站在古朴的驻地旧址,我想起闽中红旗不倒精神。
仅涵江山区,就有许许多多的革命遗址。
这些地方,是时间河流上的一个个埠头,它们联结起革命发展的脉络。
1928年3月,澳柄山区诞生了闽中地区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莆田游击队,随后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23军第207团旧址在东泉圆通寺宣告成立,队伍战斗在白沙镇澳柄宫附近一带。
澳柄宫现在是红军207团旧址。
1930年,中共莆属特委成立,红军207团改编为福建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转移新县镇外坑,年底,在宣德宫成立外坑乡苏维埃政府。
但由于力量悬殊,政权被国民党军摧毁。
此后直到1936年,闽中游击队曾一度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仍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形成以常太为中心的莆仙边游击根据地。
1936年10月,中共闽中特委转移到庄边镇宁里,直到1941年离开前往永泰,留下了如今的特委驻地旧址。
大洋乡闽中革命司令部,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闽中特委从永泰迁回大洋,改为闽中地委、闽中工委。
1949年2月,闽浙赣人民游击队闽中支队司令部在大洋乡成立。
于是,有了现在的闽中革命司令部。
革命遗址遍布涵江山区五个乡镇。
在萩芦镇官林村,则有苏华故居,人们纷纷前来瞻仰,到这位为革命事业奉献青春和鲜血的革命者故里学习。
革命遗址遍布在山里。
残酷的斗争形势,迫使革命者不得不凭借恶劣的环境条件,与敌周旋。
宁里地处莆田和永泰交界处,真是山里又山里。
后来他们一路从山里走进城里。
那时起,山里、城里、这里,那里,都一片安宁。
处处皆“宁里”。
我想象,若没有车辆相助,凭双脚,走山路,可能还要负重,今天的我们,可还能走得进宁里来?对着眼前久历风雨的老房子,我发现,它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在无声注视。
驻地旧址后面,一片茂密竹林,竹子身姿挺拔,长势昂扬,让人感受到一种精神一种气势。
当初,当革命者在这里学习、训练时,是否也有一片竹林相伴? 辞别宁里,出山里,返回城里,道路从弯曲陡峭,逐渐宽广平缓。
阳光照耀着,车窗外,近水远山透着昂扬向上的气息。
石榴花(外一章) 一串串红鞭炮,遇上阳光,一点就着,把乡村小院炸得喜气洋洋,把父亲脸上皱纹炸得一平如展,把母亲炊烟炸得节节攀高,把村姑娘爱情炸得家喻户晓,喜庆的红色,为夏日乡村嫩绿肤色涂上一层淡淡的胭脂红。
石榴花开罢,摇身变成一盏小灯笼,由青慢慢变黄,悄悄用月光酝酿一坛芬芳美酒,待到农历八月十
五,大大方方地捧出献给月老中秋。
□吴晓波 我爱石榴花,更爱它爽朗泼辣的性格,大大咧咧一笑,火辣辣的目光,让所有挂在眉梢上的颓废和萎靡弯下了腰。
我爱石榴花,更爱它平实旷达的人生态度,多少次狂风暴雨后,总是绽放枝头,绚丽成五彩缤纷的笑颜。
看着石榴花,我也想站在它们中间,开成它们中的一朵,大胆热烈地张扬着生命的美好和热爱。
月季花 玫瑰虽好,却离我总有一段悠长的距离,只可远观而不可亲。
再说,玫瑰那高昂的头颅,华丽的服饰,冷艳的表情,总是让我这只癞蛤蟆望而却步,产生几分自卑。
是你,房前檐下,路边街头,风雨无阻,总是默默伴随我的左右。
清晨,你用你灿烂的笑靥,向我第一声问好;傍晚,你用你挂在嘴角上的调皮,向我道一声珍重。
一朵朵月季花,像常年在家操持家务的妻子,可能有点土气,可能有点小脾气,可能有点唠叨,可又是那么真实美丽,摸得着一颗质朴而敦厚的心。
看着月季花,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那枝上最红的一朵,就是我那朴实贤惠的妻,今后,我要倍加珍惜,好好地呵护你。
牵牛花 牵牛花是喜庆的花。
一串串牵牛花爬上藤架,把一串串火红小喇叭挂在乡村脖子上;阳光憋足了劲,鼓起腮帮子,“滴答,滴答”吹起迎亲唢呐,在布谷清脆的伴奏下,母亲搀扶稻花姑娘,披上洁白盖头,登上风的花轿,纷纷出嫁。
牵牛花是勤劳的花。
它们和乡亲们一样,栉风沐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暗合着乡村千年不变的鼓点;它们既不想像牡丹那样雍 容华贵,也不想像兰花那样骄气矫情,只想用生命的小喇叭为辛勤耕作的乡亲们加油鼓劲。
牵牛花是幸福的花。
六月的汗水轻轻一浇,牵牛花就开了,一颗火红的心,给季节染上红彤彤的底色,父亲站在底色之上,挥舞银色镰刀,敲开一扇丰收大门。
每年入夏,牵牛花都会在我记忆河流里鲜活,笑盈盈地伸出手,引着我走进一个热火朝天、汗流浃背的夏。
MEIZHOUDAILY 2022年5月16日星期
一 书店 □方宝璋 我极少逛街,但如果逛街,一般去处就两个地方,其中之一就是逛书店。
记得在福建师大任教时,所住康山里宿舍区旁边有家晓风书店。
书店刚开张时,规模较大,面积有两百多平方米。
更令人感到惬意的是书店专卖高雅、学术性强的图书,如近代文化名人陈寅恪、胡适、吴宓等的传记,二十四史、世界学术名著译丛等。
书店的装修也很雅致,墙上挂着一对硕大的牛角、几幅字画,书店中间摆着几张靠背椅、茶几,不时还播放音量极小的西洋古典音乐。
总之,让人一跨进书店的大门,就立刻感觉到书卷气息。
由于书店紧挨着我住的宿舍区,我虽然忙,但还是不时光顾,一是看看到了什么新书,二是去享受一下温馨的书卷气息。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书店就缩小了规模,分割出一半作为服装店,书店的靠背椅、茶几等消失了。
过了一年半载,书店又缩小了规模,再分割出一半作餐饮店。
墙上的牛角、字画也消失了,四面墙壁都摆满了书架,堆着各种各样的图书,书店中间也摆着柜子,柜面上散落着琳琅满目的画册、字帖等。
整个书店只有柜子旁边两条窄窄的通道可让读者进出。
从此,我去书店的次数明显减少,因为那狭窄杂乱的空间,那闷人的气息,让人无法在店里久留。
我调到江西财大后,每年都会去莆田学院或福建税校上函授课。
两校附近,曾有两三家书店。
每当我上完课,傍晚吃饭前,就信步走到那几家书店看看。
记得第一次去逛那几家书店时,让我吃了一惊,有家席殊书店,布置虽然比不上晓风书店刚开张时的那么雅致,但也令人感觉到浓浓的书卷气息。
我惊讶在莆田那样小的城市里,竟然有这样品味的书店存在。
但是,同样好景不长,过了一两年后,我再去莆田学院上课时,发现席殊书店命运比晓风书店更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游戏机店。
自从走上治学的道路,我到了全国不少的城市。
每当我初到一座城市,总抽空上街逛一下,领略一下这座城市的风貌。
我总喜欢到这座城市的最大图书城去看看。
我觉得每座城市的图书城、书店是这座城市最直观的文化窗口。
我曾到过南方一座繁华的城市,街道上高级轿车川流不息,霓虹灯五光十色,商店里各种各样商品令人目不暇接。
但是该城最大的图书城冷冷清清,空旷的书店里只有两三个读者,书橱上摆放着《致富秘诀》《富爸爸》之类的书籍。
南方那座城市之所以书店冷冷清清,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该市虽然经济发达,但却是文化沙漠,整座城市没有一所有名的大学。
而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高校数量居全国前茅,而且又有北大、清华、人民大学等全国一流的大学,这是书店生存发展的最好环境。
对于书店与文化的关系,我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和研究。
但我感觉,或许中国书店繁荣之时,即是中国文化昌盛之日。
说墨 □李天宝 自古以来,文人就与墨结下不解的情缘。
这不,旧时农村里老人常常把有文化的人,称作肚里有“墨水”的人。
我自诩是半个文人,所以舞文弄墨是在所难免的,从这一点看,也勉强算得上一个“墨客”。
因而,我向来喜欢墨。
但要说我第一次与墨打交道,却不是起于文学,甚至不是起于书写,而是源于一种工具——墨斗。
我爷爷是个修船匠,往高大上去说,是能工巧匠鲁班门下,自然而然就有一个糊口用的鲁班工具箱。
那工具箱里,有的是刨子、锯子、斧子、尺子等。
我最喜欢的却是放在工具箱小方格里的墨斗。
之所以喜欢墨斗,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拉出墨线,能刻画下自己所想要的线条。
虽然常常因拉线时被墨汁飞溅成花猫脸而没少挨父母的骂,但我每次还是乐此不疲,等爷爷收工回家,刚放好工具箱,我就偷偷去拨弄一番。
稍大以后,墨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样充满了神奇的东西。
它不仅能用来写很漂亮的春联,还能被父母当作消炎药一样用来对付被蚊虫叮咬的包包,而最神奇的是,当有人生了一种土名“飞蛇”的皮肤病时,只要用毛笔沾墨,在墙上画一个人形,再写上“金木水火土”加一个“斩”字,就能把病治好了。
在那时的我想来,这种治病方法,不是人的功劳,而是因为墨的神奇与灵异。
大概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吧,我家刚刚盖了新房子,第一年在新居过年,按风俗,要很隆重写一厅的春联。
父母是文盲,于是,硬要我写。
父亲还连哄带骗说“:你就大胆写,以前不是有人用碗底印上去也是可以的,你写上字就行了。
”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写毛笔”的经历,也为此沾上了墨香,而没有想到,这一沾就延续了30年。
后来,每一年的写春联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的身上,为此我和墨的联系也就越发紧密起来。
我写字功底差,每每写起春联来,那字完全是野路子,但因墨的缘故,我还是常常写着写着,就会沉醉在那沁人心脾的墨香之中。
到了大学毕业,我第一次收到同学赠送的一方墨锭,心里甚为欢喜。
在此之后,我还特意对墨做了一番了解。
从而,我知道了墨一般分松烟与油烟两种,了解了古时制墨名家有五代十国时的李延硅父子,有宋徽宗赵佶,有明时程君房,有清代曹素功与胡开文等。
我后来还去古玩市场淘墨,并于2005年淘得程君房彩墨一锭,记得当时很有一番捡漏之喜,虽然后来知道那是赝品,但那过程也是不亦乐乎。
随着年岁见长,我对很多事都变得无欲无求,但对于墨的喜爱却是依旧炽热。
我还是会如之前一样,到古玩市场淘墨,因眼界与经济能力故,我常常淘回来的,都是赝品、次品,但也不气馁,还常常自我安慰说,古人云“:古墨可以当药。
”我这文学病,还真需要古墨这一剂药来医。
我后来甚至因为出于对墨的喜爱,干脆就用了粹墨木一为笔名,还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粹墨居。
说起墨来,我似乎还有很多很多话要说。
我知道,我与墨的这不解之缘是不想断了。
我希望自己能和墨定一个一世不离不弃的情缘。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