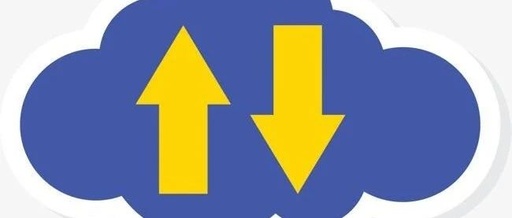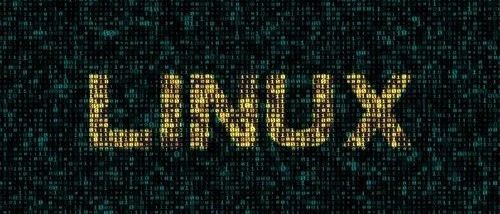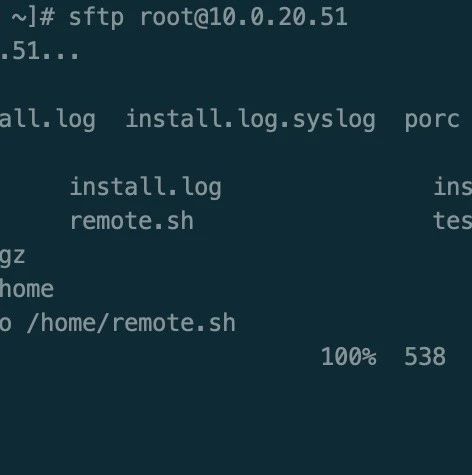2022年1月26日星期三编辑:刘秀平Email:ncdzwotu@163
在年这边,在年那边
王德亭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是乡亲们扎堆聊天的地方。
进了腊月门,人们关于过年的话题自然多起来。
“今年是大经年,还是小经年?”“大经年。
”“大经年,空儿就多一点。
”所谓大经年,就是腊月有三十;而小经年,腊月二十九就是年夜了。
所谓“有空儿”“没空儿”,还真不是无病呻吟。
在那“干到腊月二十
九,吃了包子就下手”的年月,队里总有指派不完的活儿。
社员的工夫不是自己说了算。
年总是要过的。
过年是一个迎来送往的节日,谁家没有亲来戚往呢?在年这边,就得有个准备。
赶个年集———西关集,古城集,猪肉、带鱼、鲅鱼、海带,山药、土豆、黑蘑菇、韭黄,该买的,日子再窘迫也得想想办法。
那个时候,谁家有冰箱冰柜肯定“不是一般人物”。
没有冰箱,买回的肉鱼自有存放处,在背阴的南墙上钉个橛子,鱼啊肉啊挂在上面,天越冷越攒劲。
那年月, 冷的时候多,这个天然冰箱可搁多少东西啊! 腊月里的每一天特当一天过,腊月里的每一天都要掐着钟点过。
一进腊月门,父亲会到供销社截上平纹布或斜纹布,找邻居做缝纫的姐姐给我做身衣服。
套在棉衣外面,就“见新”了。
腊月二十
三,灶王爷上九天述职。
辞灶过了,父亲便带我们扫屋。
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
“辞旧”的序曲已吹响了。
过了腊月二十
三,每个日子前都可以冠上年:年二十
四,年二十五……年二十
九,年三十……好像辞了灶,年就名正言顺了。
为什么冠以“年”字呢,也许过了辞灶,年就一天比一天近了。
年初二是大日子,有新女婿的伺候新女婿,没有女婿的招待外甥———从这天起,人来客去,热热乎乎。
总不能旋上轿旋扎耳朵眼吧,所以准备工夫都在年前。
年二十六
七,父亲就开始蒸发面干粮。
父亲揉面,我拉风箱,过年总要蒸 几锅馒头卷子。
头一锅出笼,香气漫了一屋子。
香,这解馋的气味啊!大筐装,小箱盛,唯恐哪个还不满。
过了年,天气回暖早,干粮吃不及便生出霉斑。
在穷日子里泡透了,谁舍得扔掉!馏馏剥了皮儿照样吃。
———我不愿意以今天的眼光比量过去的事情,我理解父亲的苦心。
父亲的忙碌有时是见缝插针,写春联却不能,要看人家的工夫。
父亲会拿出上好的红纸,嘱我找谁谁去写———他早给人打过招呼。
如果人家忙不开,我就放下红纸,过一两天再来。
如果正好有空儿,他会裁好纸,让我按牢纸边,他便龙飞凤舞起来。
他不看书本,挥毫泼墨———对联都装在肚子里了。
奇怪的是,原本没精打采一张红纸,一旦写成对联就来了精神。
他看了我的眼神,说,你也能写,大街上张的红榜我看了,你在班里排前
三,高材生。
写毛笔字,写对子,跟学习好歹实在没有多少关系,这是若干年以后我的体会。
父亲说,掉不过腚来就是一天。
明明是过了冬至一天比一天长了,怎还不够忙呢?有人抬杠:“你是找忙。
你伸手不动,看看年能不能过!”“那不一样。
” 除夕这天,父亲还是一个字“忙”!到了炸丸子炸肉蛋的时候 了。
拿下一个干粮垫子,揭两个煎饼垫底儿。
搅好面糊,放进切好的肉块、鱼块或山药、土豆,挂上面糊,便可下锅了。
头一笊篱捞出来,晾在干粮垫子里,香得让我直咽口水。
上坟祭祖,回来再贴春联。
父亲下一碗水饺,捞出锅,分到三个碗里,同酒、烟、茶、烧纸放进箢子,令我们去给娘、爷爷和奶奶上坟。
父亲说:“你娘生你不容易。
你一岁半成了没娘孩子。
到坟上,好好跟娘说,也吃上了也穿上了,叫她啥也不要牵挂。
” 除夕之夜,没有春晚节目可看,连台电视机也没有。
一家人围着案板包水饺。
我团剂子,父亲擀皮儿,哥哥包水饺。
父亲一面忙,一面低声讲古,有一个人一辈子自己过。
人家过年是“添碗添人眼”,可他呢,一双筷子,筷子尖磨成了锥把儿,碗底磨得溜光蹲不住了。
年夜里,他一个人熬不过,跟筷子和碗打起来了。
父亲说:“有了人才有财,财是人创造的。
穷没有穷到底的,富也没有扎下根的。
”这成为我的精神财富,鼓舞着我自立做人。
年夜里静悄悄的。
水饺包好了,父亲催我们去睡觉。
他在盖垫上撒一层面粉,将水饺重新摆放一过,防备黏连。
第二天,他唤醒我们。
吃过水饺,天也亮了,该去为长辈拜年了。
父亲也有几个长辈需要去拜年。
我听父亲说:“我磕的头又少了一个!一年少得一年了。
”里面埋着“又有谁走了”“我也老了”的话,我能听出来。
光阴催人,如今我也有了这种感觉。
年又有“年关”之称。
俗话说“穷人过关,富人过年”,意思是欠债还钱,到了年节你欠人的总要还。
“穷怕亲戚富怕贼”,再穷,亲友上门也要拿出心来伺候。
故,父亲忙的“穷年”我未敢忘。
“年”是什么呢?似乎看不见,摸不着。
就以人的“年龄”而论,是先有年后有了年龄呢,还是先有年龄后有“年”呢?这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命题。
人间世还有很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破解。
少年盼年,除了“穿新衣,戴新帽,走姥娘家放鞭炮”以外,还有对成长的渴望。
人都要往大里长,小孩儿长大,大人变老。
年可不是任人驱遣的东西,她不会因为你的欢迎就加紧跑几步,也不会因为你的拒斥而停驻几天。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从年前到年后,我们谁也别想停下来,也停不下来。
那就走吧,一直往前走。
陪伴 鲁北 年味是什么?留在我们记忆里的是贴春联、贴门神、剪窗花、放爆竹、吃好的、穿好的。
丰子恺在《过年》中写道:年底这一天,是准备通夜不眠的。
梁实秋在《北平年景》中写道:祭祖先是过年的高潮之
一,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
孙犁在《记春节》中写道:春节从贴对联开始。
肖复兴在《年味儿》中写道:从腊月二十三之后到年三十的日子里,每一天都不能够闲着,都安排好了关于年夜饭的密密麻麻的节目单。
由此可见,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地域不同,习俗却差不多,各家都在忙忙乎乎,红红火火。
年年过年,年年过,似乎大人小孩都在盼着这一天。
我是1987年3月结婚的,第二年,父母把我们分出去,另起了炉 灶。
一个家,分成了两个家。
几年之后,弟弟也结了婚。
没过多久,也把他们分出去,两个家成了三个家。
农忙的时候,母亲做饭,下地归来,在一起吃饭。
农闲的时候,各家做各家的。
年夜饭是团圆饭。
年夜饭的大厨,父亲是首选。
他扎上围裙,煎、炒、烹、炸,满屋子弥漫着馨香,不一会儿,七八个色香味俱佳的菜肴端上了饭桌。
父亲解下围裙,在小桌前坐下,我们兄弟俩也坐下。
我给父亲斟满一杯酒,接着,给我和弟弟也斟满。
我们喝将起来,谁也不监督谁。
“父子不同席,叔侄不对饮”已经成为过去。
喝完第三杯,我问父亲,还喝么?父亲说,依你们。
我说,过年嘛,再喝一杯吧,父亲说,行。
我又斟满了三杯。
那些年,父亲的酒量和 我们兄弟俩相当。
父亲过了70岁,酒量远远被我们兄弟俩落下了。
喝完两杯,父亲就斩酒了。
我们继续喝我们的,他坐在桌边看着。
席间,我们会聊聊一年的收成,说说今后的打算。
酒足饭饱之后,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陪父亲说话。
母亲和我的妻子、弟媳包饺子。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包饺子。
我的两个妹妹长大了,帮着母亲包饺子,我父亲就不干包饺子的营生了。
再后来,两个妹妹陆续嫁出去,包饺子的任务落到了母亲和我的妻子、弟媳的身上。
年初一的饺子是父亲煮熟的。
我还没有进城的那些年,我和妻子、弟弟、弟媳,准时到父母家吃饺子。
以后我和妻子进了城,回家就睡在父母的炕上。
弟弟和弟媳还是遵循老规矩,6点准时到父母家吃饺子。
我结婚35年了,弟弟结婚也30多年。
这些年来,我们都是陪着父母吃大年初一的饺子的。
年味就是陪伴的味道。
现在每到过年,总有人感叹没有年味,过年没意思。
在我看来,发出这种感叹的,都是没有忙年,只等着过年的人。
而年味,恰恰是忙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在老家,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就拉开了忙年的序曲,扫房子、磨豆腐、蒸馒头、杀鸡割肉炸丸子,都需要在大年三十之前这短短七八天的时间完成,所以才叫“忙年”,重点落在一个“忙”字上。
大人忙,孩子也不闲着。
东家做豆腐缺张滤豆浆的纱布,打发孩子去二婶家借;西家蒸馒头缺个大号的蒸屉,打发孩子去大娘家拿。
这时候的孩子,绝对不会不听使 忙出来的年味 苑广阔 唤,而是满心欢喜地东家进、西家出,心里充满了新年的喜悦。
做豆腐、蒸馒头,都需要大火伺候炉灶。
家里的男人,举着一把斧头在门口劈柴,杨树根,柳树根,张牙舞爪,难劈得很,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一些人干脆脱了外面的棉衣,干活更轻便。
女人在厨房里也是忙得团团转,孩子在灶前卖力地拉着风箱,伴随着风箱的“呼呼”声,火苗不时窜出灶口,贪婪地舔舐着锅沿,好像也知道锅里是诱人的豆腐和馒头。
热气蒸腾中,一板又一板雪白的豆腐出锅了,一屉又一屉雪白的 馒头,也出锅了。
不大的农家小院,被豆腐的清香、馒头的面香填满,家家如此,户户如
一。
最热闹的是腊月二十
七,这天家家户户要杀鸡炸丸子。
二大爷老花眼,二大娘明明让他抓那只芦花鸡来杀,结果他折腾半天,抓了一只披着七彩羽冠的大公鸡,被二大娘一阵埋怨。
二大爷也不恼,嘻嘻笑着,继续抓鸡。
三叔杀鸡的技术不敢恭维,明明已经“被杀”的公鸡,一边发出凄厉的叫声,一边满院子飞奔,害得三叔一家跟在公鸡屁股后面追。
最后,公鸡干脆跳上墙头,进了邻居二爷爷的院子。
说是二爷爷,不 过是辈分大,年龄也不比三叔大几岁。
这下好,本来一家人抓鸡,变成了两家人抓鸡,二爷爷一边嘲笑三叔的杀鸡技术,一边拾起一根木棒子,一下子就把公鸡击倒在地。
二爷爷放了一辈子羊,扔石头赶羊,准得很。
鸡肉剁成小块,放盐腌制备用。
和一盆面,里面葱花、花椒、茴香、八角粉一应俱全,把腌制好的鸡肉块裹着面糊糊,放进沸腾的油锅,随着“嗞拉嗞拉”的声音,一股香气扑鼻而来。
炸鸡丸子是孩子的最爱,热乎乎的炸鸡丸子,一口气可以吃上七八个。
除了炸鸡,也有人家炸带鱼、炸茄盒子、炸萝卜丸子……炸什么全凭家人喜好。
这些被家乡人称为“炸货”的美食,放在室外或偏房里,可以一直吃到出正月。
过年离不开一个“吃”字,豆腐做好了,馒头蒸好了,鸡啊鱼啊炸好了,忙年也就忙得差不多了。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写春联。
乡村集市上也有卖春联的,讲究一点的人家,还是会请村里有文化、书法好的人自己来写,似乎只有自己动手写的春联,才是真正的春联。
年除夕一大早,第一件事就是贴春联。
大红的春联,五颜六色的“罗门钱”,到处都可以贴的“福”字,让整个村庄犹如一个漂亮的姑娘经过精心的打扮,穿上了漂亮的衣裳,更加楚楚动人。
一切都准备好了,年也真的来了。
进了腊月门,人们关于过年的话题自然多起来。
“今年是大经年,还是小经年?”“大经年。
”“大经年,空儿就多一点。
”所谓大经年,就是腊月有三十;而小经年,腊月二十九就是年夜了。
所谓“有空儿”“没空儿”,还真不是无病呻吟。
在那“干到腊月二十
九,吃了包子就下手”的年月,队里总有指派不完的活儿。
社员的工夫不是自己说了算。
年总是要过的。
过年是一个迎来送往的节日,谁家没有亲来戚往呢?在年这边,就得有个准备。
赶个年集———西关集,古城集,猪肉、带鱼、鲅鱼、海带,山药、土豆、黑蘑菇、韭黄,该买的,日子再窘迫也得想想办法。
那个时候,谁家有冰箱冰柜肯定“不是一般人物”。
没有冰箱,买回的肉鱼自有存放处,在背阴的南墙上钉个橛子,鱼啊肉啊挂在上面,天越冷越攒劲。
那年月, 冷的时候多,这个天然冰箱可搁多少东西啊! 腊月里的每一天特当一天过,腊月里的每一天都要掐着钟点过。
一进腊月门,父亲会到供销社截上平纹布或斜纹布,找邻居做缝纫的姐姐给我做身衣服。
套在棉衣外面,就“见新”了。
腊月二十
三,灶王爷上九天述职。
辞灶过了,父亲便带我们扫屋。
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
“辞旧”的序曲已吹响了。
过了腊月二十
三,每个日子前都可以冠上年:年二十
四,年二十五……年二十
九,年三十……好像辞了灶,年就名正言顺了。
为什么冠以“年”字呢,也许过了辞灶,年就一天比一天近了。
年初二是大日子,有新女婿的伺候新女婿,没有女婿的招待外甥———从这天起,人来客去,热热乎乎。
总不能旋上轿旋扎耳朵眼吧,所以准备工夫都在年前。
年二十六
七,父亲就开始蒸发面干粮。
父亲揉面,我拉风箱,过年总要蒸 几锅馒头卷子。
头一锅出笼,香气漫了一屋子。
香,这解馋的气味啊!大筐装,小箱盛,唯恐哪个还不满。
过了年,天气回暖早,干粮吃不及便生出霉斑。
在穷日子里泡透了,谁舍得扔掉!馏馏剥了皮儿照样吃。
———我不愿意以今天的眼光比量过去的事情,我理解父亲的苦心。
父亲的忙碌有时是见缝插针,写春联却不能,要看人家的工夫。
父亲会拿出上好的红纸,嘱我找谁谁去写———他早给人打过招呼。
如果人家忙不开,我就放下红纸,过一两天再来。
如果正好有空儿,他会裁好纸,让我按牢纸边,他便龙飞凤舞起来。
他不看书本,挥毫泼墨———对联都装在肚子里了。
奇怪的是,原本没精打采一张红纸,一旦写成对联就来了精神。
他看了我的眼神,说,你也能写,大街上张的红榜我看了,你在班里排前
三,高材生。
写毛笔字,写对子,跟学习好歹实在没有多少关系,这是若干年以后我的体会。
父亲说,掉不过腚来就是一天。
明明是过了冬至一天比一天长了,怎还不够忙呢?有人抬杠:“你是找忙。
你伸手不动,看看年能不能过!”“那不一样。
” 除夕这天,父亲还是一个字“忙”!到了炸丸子炸肉蛋的时候 了。
拿下一个干粮垫子,揭两个煎饼垫底儿。
搅好面糊,放进切好的肉块、鱼块或山药、土豆,挂上面糊,便可下锅了。
头一笊篱捞出来,晾在干粮垫子里,香得让我直咽口水。
上坟祭祖,回来再贴春联。
父亲下一碗水饺,捞出锅,分到三个碗里,同酒、烟、茶、烧纸放进箢子,令我们去给娘、爷爷和奶奶上坟。
父亲说:“你娘生你不容易。
你一岁半成了没娘孩子。
到坟上,好好跟娘说,也吃上了也穿上了,叫她啥也不要牵挂。
” 除夕之夜,没有春晚节目可看,连台电视机也没有。
一家人围着案板包水饺。
我团剂子,父亲擀皮儿,哥哥包水饺。
父亲一面忙,一面低声讲古,有一个人一辈子自己过。
人家过年是“添碗添人眼”,可他呢,一双筷子,筷子尖磨成了锥把儿,碗底磨得溜光蹲不住了。
年夜里,他一个人熬不过,跟筷子和碗打起来了。
父亲说:“有了人才有财,财是人创造的。
穷没有穷到底的,富也没有扎下根的。
”这成为我的精神财富,鼓舞着我自立做人。
年夜里静悄悄的。
水饺包好了,父亲催我们去睡觉。
他在盖垫上撒一层面粉,将水饺重新摆放一过,防备黏连。
第二天,他唤醒我们。
吃过水饺,天也亮了,该去为长辈拜年了。
父亲也有几个长辈需要去拜年。
我听父亲说:“我磕的头又少了一个!一年少得一年了。
”里面埋着“又有谁走了”“我也老了”的话,我能听出来。
光阴催人,如今我也有了这种感觉。
年又有“年关”之称。
俗话说“穷人过关,富人过年”,意思是欠债还钱,到了年节你欠人的总要还。
“穷怕亲戚富怕贼”,再穷,亲友上门也要拿出心来伺候。
故,父亲忙的“穷年”我未敢忘。
“年”是什么呢?似乎看不见,摸不着。
就以人的“年龄”而论,是先有年后有了年龄呢,还是先有年龄后有“年”呢?这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命题。
人间世还有很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破解。
少年盼年,除了“穿新衣,戴新帽,走姥娘家放鞭炮”以外,还有对成长的渴望。
人都要往大里长,小孩儿长大,大人变老。
年可不是任人驱遣的东西,她不会因为你的欢迎就加紧跑几步,也不会因为你的拒斥而停驻几天。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从年前到年后,我们谁也别想停下来,也停不下来。
那就走吧,一直往前走。
陪伴 鲁北 年味是什么?留在我们记忆里的是贴春联、贴门神、剪窗花、放爆竹、吃好的、穿好的。
丰子恺在《过年》中写道:年底这一天,是准备通夜不眠的。
梁实秋在《北平年景》中写道:祭祖先是过年的高潮之
一,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
孙犁在《记春节》中写道:春节从贴对联开始。
肖复兴在《年味儿》中写道:从腊月二十三之后到年三十的日子里,每一天都不能够闲着,都安排好了关于年夜饭的密密麻麻的节目单。
由此可见,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地域不同,习俗却差不多,各家都在忙忙乎乎,红红火火。
年年过年,年年过,似乎大人小孩都在盼着这一天。
我是1987年3月结婚的,第二年,父母把我们分出去,另起了炉 灶。
一个家,分成了两个家。
几年之后,弟弟也结了婚。
没过多久,也把他们分出去,两个家成了三个家。
农忙的时候,母亲做饭,下地归来,在一起吃饭。
农闲的时候,各家做各家的。
年夜饭是团圆饭。
年夜饭的大厨,父亲是首选。
他扎上围裙,煎、炒、烹、炸,满屋子弥漫着馨香,不一会儿,七八个色香味俱佳的菜肴端上了饭桌。
父亲解下围裙,在小桌前坐下,我们兄弟俩也坐下。
我给父亲斟满一杯酒,接着,给我和弟弟也斟满。
我们喝将起来,谁也不监督谁。
“父子不同席,叔侄不对饮”已经成为过去。
喝完第三杯,我问父亲,还喝么?父亲说,依你们。
我说,过年嘛,再喝一杯吧,父亲说,行。
我又斟满了三杯。
那些年,父亲的酒量和 我们兄弟俩相当。
父亲过了70岁,酒量远远被我们兄弟俩落下了。
喝完两杯,父亲就斩酒了。
我们继续喝我们的,他坐在桌边看着。
席间,我们会聊聊一年的收成,说说今后的打算。
酒足饭饱之后,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陪父亲说话。
母亲和我的妻子、弟媳包饺子。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包饺子。
我的两个妹妹长大了,帮着母亲包饺子,我父亲就不干包饺子的营生了。
再后来,两个妹妹陆续嫁出去,包饺子的任务落到了母亲和我的妻子、弟媳的身上。
年初一的饺子是父亲煮熟的。
我还没有进城的那些年,我和妻子、弟弟、弟媳,准时到父母家吃饺子。
以后我和妻子进了城,回家就睡在父母的炕上。
弟弟和弟媳还是遵循老规矩,6点准时到父母家吃饺子。
我结婚35年了,弟弟结婚也30多年。
这些年来,我们都是陪着父母吃大年初一的饺子的。
年味就是陪伴的味道。
现在每到过年,总有人感叹没有年味,过年没意思。
在我看来,发出这种感叹的,都是没有忙年,只等着过年的人。
而年味,恰恰是忙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在老家,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就拉开了忙年的序曲,扫房子、磨豆腐、蒸馒头、杀鸡割肉炸丸子,都需要在大年三十之前这短短七八天的时间完成,所以才叫“忙年”,重点落在一个“忙”字上。
大人忙,孩子也不闲着。
东家做豆腐缺张滤豆浆的纱布,打发孩子去二婶家借;西家蒸馒头缺个大号的蒸屉,打发孩子去大娘家拿。
这时候的孩子,绝对不会不听使 忙出来的年味 苑广阔 唤,而是满心欢喜地东家进、西家出,心里充满了新年的喜悦。
做豆腐、蒸馒头,都需要大火伺候炉灶。
家里的男人,举着一把斧头在门口劈柴,杨树根,柳树根,张牙舞爪,难劈得很,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一些人干脆脱了外面的棉衣,干活更轻便。
女人在厨房里也是忙得团团转,孩子在灶前卖力地拉着风箱,伴随着风箱的“呼呼”声,火苗不时窜出灶口,贪婪地舔舐着锅沿,好像也知道锅里是诱人的豆腐和馒头。
热气蒸腾中,一板又一板雪白的豆腐出锅了,一屉又一屉雪白的 馒头,也出锅了。
不大的农家小院,被豆腐的清香、馒头的面香填满,家家如此,户户如
一。
最热闹的是腊月二十
七,这天家家户户要杀鸡炸丸子。
二大爷老花眼,二大娘明明让他抓那只芦花鸡来杀,结果他折腾半天,抓了一只披着七彩羽冠的大公鸡,被二大娘一阵埋怨。
二大爷也不恼,嘻嘻笑着,继续抓鸡。
三叔杀鸡的技术不敢恭维,明明已经“被杀”的公鸡,一边发出凄厉的叫声,一边满院子飞奔,害得三叔一家跟在公鸡屁股后面追。
最后,公鸡干脆跳上墙头,进了邻居二爷爷的院子。
说是二爷爷,不 过是辈分大,年龄也不比三叔大几岁。
这下好,本来一家人抓鸡,变成了两家人抓鸡,二爷爷一边嘲笑三叔的杀鸡技术,一边拾起一根木棒子,一下子就把公鸡击倒在地。
二爷爷放了一辈子羊,扔石头赶羊,准得很。
鸡肉剁成小块,放盐腌制备用。
和一盆面,里面葱花、花椒、茴香、八角粉一应俱全,把腌制好的鸡肉块裹着面糊糊,放进沸腾的油锅,随着“嗞拉嗞拉”的声音,一股香气扑鼻而来。
炸鸡丸子是孩子的最爱,热乎乎的炸鸡丸子,一口气可以吃上七八个。
除了炸鸡,也有人家炸带鱼、炸茄盒子、炸萝卜丸子……炸什么全凭家人喜好。
这些被家乡人称为“炸货”的美食,放在室外或偏房里,可以一直吃到出正月。
过年离不开一个“吃”字,豆腐做好了,馒头蒸好了,鸡啊鱼啊炸好了,忙年也就忙得差不多了。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写春联。
乡村集市上也有卖春联的,讲究一点的人家,还是会请村里有文化、书法好的人自己来写,似乎只有自己动手写的春联,才是真正的春联。
年除夕一大早,第一件事就是贴春联。
大红的春联,五颜六色的“罗门钱”,到处都可以贴的“福”字,让整个村庄犹如一个漂亮的姑娘经过精心的打扮,穿上了漂亮的衣裳,更加楚楚动人。
一切都准备好了,年也真的来了。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