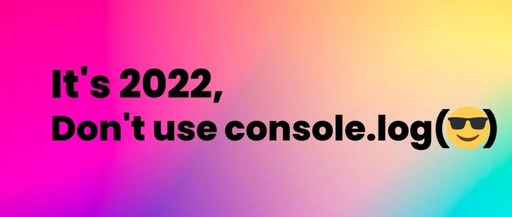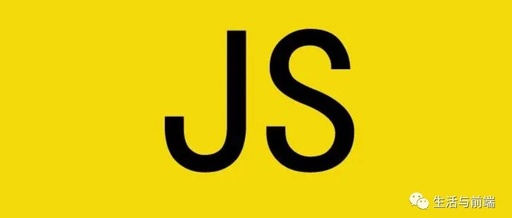2012年8月21日星期二Tel(押010)62569455
网谈
主编:张其瑶校对:王心怡E-mail押qyzhang@
3 >>>本期关键词:制度 图片来源:/ 人情社会与制度选择 姻马亮 制度选择的问题实在是涉及方方面面,我的日常观察和学术训练告诉我,中国作为关系取向的人情社会,在治理制度的许多方面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以美国、英国等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差异明显,而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领域的表现较为明显。
举个例子。
有一次去美国某大学开会,在那里攻读公共管理博士的华人学生就告诉我,他们从student转为candidate(攻读学位者)前需要通过三门考试,一门是各门课程的综合考查,闭卷限时完成;另外两门则由导师和本专业领域的专家出题,开卷限时完成。
显然,为了公平起见,老师在评阅学生试卷时应该盲审,否则自己指导的学生就可能获得不当之利,在起点上不公平。
但实际上导师为自己的学生出题时并不会徇私,而是会非常严格地对学生进行考查,如果不合格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学生“放倒”。
两门考试后进行选题答辩(proposaldefense),通过这些考查后就成为candidate,可以考虑完成学位论文了。
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由学生的导师担任,成员则由学生根据所在领域的研究状况提名专家,然后由导师确认。
所以学位答辩委员会几乎是清一色的“亲友团”,一般认为不会为难学生。
他们也没有国内越来越重视的盲审,谁审谁的论文都是一清二楚。
这种制度安排显然是建立在充分的互信基础之上的,否则 如果对任何一方不信任,都无法建立这样一种制度。
另外,导师和学生的声誉机制也发挥重要作用,如果导师让学生滥竽充数,那么传出去影响肯定不好。
反之,如果学生舞弊,这样一个污点一旦被发现,则名誉扫地,甚至会毁了一世清名,有时候连学位也会被追回。
由此看来,中国制度的基础就是对人的不信任,哪怕对教授、博士生也不能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总会钻营取巧,所以在论文答辩以后还要进行盲审,因为答辩的老师都是“托”,他们可能包庇,所以要再次核验。
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让博士生们过五关斩六将,有时候到最后一关也可能被放倒。
比较而言,反倒不如通过资格考试,在一两年内告诉你,你可能不适合攻读博士和进行学术研究,毕竟长痛不如短痛。
看到许多煎熬到6~8年才被告知可能无法拿到学位的学长们,这种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显然是令人生畏的。
最近看到有博文探讨博士生期间是否应该发表论文以及发表多了是否合适的问题,显然也与此有关。
因为大学里里外外都很难找到可以公正评判的人选,那么索性通过“社会评价”来进行,寄希望于学术期刊的评审机制可以为大学鉴别学生的研究能力,与此同时也为大学在排名时通过论文发表而加分提供口实。
但国内学术期刊也落入类似的怪圈难以自拔,更何况为大学分忧。
另一个例子就是高等教育入学资格的选拔。
中国高考制度历来褒贬不
一,褒者认为它公平,一把尺子,为社会流动打开了大门;贬者指责它是应试教育的根源,单纯考查智育,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试点自主招生,但其模式与高考无异,只不过在最后环节会设定一个面试,并据此刷掉许多考生。
针对自主招生的观点也和针对高考一样,有认为它矫枉过正的,也有批评它为权势人士大开方便之门的。
我们也看到发达国家会有高考制度,但学生日常表现的考查也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有时候甚至会成为关键因素。
这种制度安排建立在大学对高中的信任上,即可以将高中老师的记录作为评判依据。
而在中国,高中老师的表现记录通 常是难以令人相信的,即便是大学老师为留学生写的推荐信也很难令人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统一考试的权重、降低日常表现记录的权重,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制度选择。
由此联想到国内大学有关同行评议和科学计量学的争论。
现在大学绩效考核、职称评定等都严重依赖科学计量指标,过度量化的考核被人们认为不利于学术界的良性发展,而年度考核的周期安排也诱发短期主义,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许多大学试点助理教授职位,希望通过跨年综合考核来对教师进行指导。
这显然是受到发达国家高校的启发,即为 新进教师留有一个空间,使其可以通过扎实的研究证明自己的能力,然后为其提供tenure(终身职位)。
但如果评审专家徇私,这种制度就很难持续下去,反而不如科学计量学指标来得客观。
也正因为人情社会难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纯粹客观量化的考核就更容易为人接受。
学术期刊评审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最近看了一些研究,发现同行评议是否匿名对评议结果的影响并不大,启示我们匿名评审并不是绝对有效的,我们的制度改革方向可能是矫枉过正。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在发达国家情境下进行的研究,如果在中国,我想可能结果会发生变化。
所以,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社会就为我们选择了适合其社情民意的制度,这种制度只有站在比较的视角下才能评判其优劣和合适与否。
简单地比较就可以发现,制度选择的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非常明显,而如果忽视了这些情境的决定意义,可能会误导制度改革者的视线,并会导致难以预料的不良影响。
因此,在批评我们的社会制度难以尽如人意的同时,我们需要看到,这是社会情境为我们提供的次优选择,因为最优选择的社会条件尚不具备,除非我们改变这种社会条件,否则我们只能接受它或进行更加艰苦的制度创新。
(/u/mliang) 赵汀阳在《博弈问题的哲学分析》(《读书》,2003年第2期)一文中说: 互相不信任和互相视为坏人的共同知识结果就把人真的变成坏人,把本来不确定的丰富世界变成确定的坏世界———我们不能忽视知识的这种生产力……在生产公正的规则的同时生产出坏的世界,这无论如何是个严重的问题。
在今天这个虽然坏但是远远还不是最坏的现实世界里,人们已经建立了相当好的制度,但还是很容易发现,所有人都想从制度中获得好处(这是制度所以获得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所有人都更想钻制度的空子(这是制度所以获得支持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所以落后国家的腐败和发 制 度 姻武 是 夷山 个 大 筐 达国家如美国的大公司丑闻都不足 为奇。
制度总是被设想为来限制别 人的利益的,而自己时刻准备着成为例外的受益者。
孔子所以提倡仁,无非是希望复杂的人际关系 能变成如同二人关系那样单纯。
博主:赵汀阳这番话,除了“所有人”的表达过于 绝对外,还是很深刻的。
我国很多人有一种“制度迷 信”,一方面,它表现为将制度看成中国所有问题的 总根源,有些人在内心深处甚至觉得,中国的制度不 发展到美国那么“先进”,就没有希望
;另一方面,它 表现为一些人将制度不佳作为自己行为不端的挡箭 牌,例如有人说:我为什么要数据造假?是为了发表 论文,不发表论文就拿不到博士学位。
是“不发表论 文就没有资格答辩”这一制度规定逼着我造假的,我 没有责任,制度有责任。
这样的逻辑居然还能获得
一 定的同情。
于是,制度成了一个大筐,什么东西都可以扔进 去。
为什么“三农”问题解决不了?制度问题。
为什么 学术不端行为那么猖獗?制度问题。
为什么中国出不 了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制度问题。
反正什么都是制度 问题,就是“我”没有问题“,我”没有责任。
不是制度不重要,但是不能迷信制度。
我在博文
《处理超越性问题的三种方式》(http: ///m/user_content.aspx?
id=44243) 中曾说: 美国著名媒体批评者、社会学家、学者和作家 Herbert
I.Schille(r1919~2000)1973年在《心智管理 者》(TheMindManagers)一书中说:“人性被看成是 什么样的,最终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因为 人类不得不那样行事,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被期 望着那样行事。
”他的意思是,如果认为人性恶,这
一 看法会影响人的行为,不是因为人必然做坏事,而是 因为“人性恶”的判断好像就期望人们去做坏事。
反 之亦然。
赵汀阳所说的“互相不信任和互相视为坏人的 共同知识结果就把人真的变成坏人”,与
Schiller的 意思是接近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Schiller的潜台 词是:“人性善”的假设更可取。
那么,赵汀阳最后也 回到了认为“人性善”的孔子这里,也就不奇怪了。
我 猜想,2000多年前的孔子,还没有复杂到“希望复杂 的人际关系能变成如同二人关系那样单纯”那种程 度。
但是,赵汀阳对“仁”的这一别解倒也很有意思。
(/u/Wuyishan) 制 度 与 美 德 姻
胡 哪 荣桂 个 更 重 要 在谈论学术不端事件和中国科技界的种种问题时,人们常说一些科学家不讲道德或没有起码的道德底线,但我时常在想,到底什么重要?是美德,还是制度? 科学家必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是大家的期望。
因为大家都认为科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纯粹的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每个科学家都应该如此,即使不是,也应该学习变成这样的人。
我们国家还一直宣扬科学家群体是有美德或讲道德之类,具有高尚风格,注重奉献的人。
但这些所谓的美德是非常不保险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科学家都有高尚的道德、都是活的圣人贤人等等,也不是所有的人天生就愿意做高尚的人,做有美德的人。
科学家更多的是普通人,更多的是经受不了各种诱惑的普通人。
而更为重要的是,讲美德只可以让有美德的人当好人,做好事,做不违背道德的事,那些没有道德,不讲道德的人是不受这些所谓的道德约束的。
所以制度应该比宣扬美德更靠谱,制度可以让那些不想当好人、做有道德的人 变得有德一些,也可以让那 些可做好人也可能做恶人的人弃恶扬善做好 人、做有道德的人。
即制度可以让更多的人有 德。
若人心不向善,人们的行为一再触犯道德 底线,那一定是制度出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只能从制度入手。
当一个科学的、刚性的、不因人而异不徇私 的制度建立起来时,讲道德懂道德的人就会多 起来。
而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社会,总要他人讲 美德、讲道德、讲仁义等等,都是一
件很可笑的 事。
故窃以为制度,不是口中说说而已的制度, 是当今中国社会最为需要的。
有了好的制度,美 德自然会来到我们身边,有了好的制度中国才 会和谐。
(/u/Ecosinic) 如何划分制度的责任与人的责任 姻金拓 事实上
,对于中国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比其他有科学研究这回事的国家严重恐怕没有太多的争论。
谈到原因,应该强调制度的原因还是人的原因却有相反的意见。
我更强调制度的原因,理由如下: 1)在中国揭露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的风险大于实践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的风险。
注意,不是说揭露方一定不成功,而是说揭露方要冒着更大的风险,付出更大的精力,却面对几率更小的成功。
新语丝上揭露过的有根据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中被处理的是极少数,敢实名来揭露的更少。
制度在为哪一方背书一目了然。
2)不错,坏制度下杀人放火仍然绝对是个人的犯罪。
但是一个社会,其犯罪率大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大于同一国家的其他时代,这个“大于”的责任便在制度。
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参考消息》上登过一则消息,一天晚上纽约市停电15分钟,其间偷盗、强奸犯罪活动剧增。
这15分钟之内和之外生活在纽约的人们没有变,但是光明和黑暗下的犯罪率截然不同。
我国当下的学术界便是这样。
不能拿坏制度下个人必须对自己的杀人放火负责来转移坏制度造成杀人放火的比例增高的责任。
3)前段时间网上有人统计过官员和非官 员的犯罪率分别为1/200和1/400,官员高于非官员。
官员犯罪率高说明官员的选拔上负筛选的成分大,而一个社会对于官员的负筛选成分大,一定是制度出了问题。
对于学者的负筛选成分大也是一样的。
4)不错,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也是人干的,说到底还是人成为决定因素。
问题恰恰在这里,即“人”当中包括了握有改变或维护制度的权力的人们,及完全没有权利染指制度的人们。
我们在讨论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时,其实质正是追究握有改变制度权力的人们还是不握有这个权力的人们,谁更该对中国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负责。
我们说“制度更应该强调” 时正是说给有改变制度权力的人们听的。
我们希望他们不但能够听到制度的弊端,而且能意识到更多的人们也已经了解了制度的弊端。
5)也许,我们的讨论与混到有权力改善制度的位置并改善之相比实在是空谈。
但是,混到一定的位置而且不改初衷的难度,未见得小于鼓励已经混到那样的位置的人们改变初衷。
况且,无论是为改变之而混上去还是混上去才想改变之,意识到更多的人希望改变都是必要的。
我们众人在希望这个层次上尚且语无伦次应该不是一件好事。
话说到这份儿上,应该清楚了吧?(/u/jintuo) “个别说明不了一般”vs制度设计 姻曹广福 这是个富有争议的话题,我认为现在由一种观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不赞成门第观念,特别是很多用人单位招聘人才的基本条件中非“211”“、985”高校不要,有些单位干脆高挂媚外牌子:“非海龟不要”,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愚蠢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起了非“211”、“985”高校毕业生的众怒,二是的确有可能错过了出身“卑微”但真正优秀的人才。
我曾经对一个领导说:“你们自己培养的优秀生都不想要,你还指望谁要你的学生?”你可以在实际操作时侧重于“211”、“985”高校,例如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出身好一点的人才,这么做大家还是能理解的,因为“211”、“985”大学与地方大学除了生源上的差别,师资的差别也是不容忽视的,而这种差别决定了学生的学术素养与眼界的差别。
见过一所地方大学的招聘条件,应聘者必须是重点大学具有国家重点学科专业的博士或者海外博士。
这个条件中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误认为只要是海外的博士就是优秀者。
我见过一些海龟,有大牛,也有平庸者,有些用人单位既然把国内人才分成了三六九等,为什么不把海龟也分 一分呢?崇洋媚外心理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用人单位在聘人问题 上的确不应该有门第等级观念,说得好听点是门第观念,说得难听一点是狗眼看人低。
话说回头,出身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综合素质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虽然我们一贯抨击今天的中小学教育,把聪明孩子教笨了,但即使是今天这样的教育体制,好学生与差学生还是能区分出来的,你高兴听或者不高兴听都否认不了这个事实。
可能有人会质疑什么是好学生什么是差学生,这也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姑且以综合素质论吧。
也许有人会以高分低能反驳我,高分低能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同样的教育体制与条件下,个别或许有例外,整体而言,高分者比低分者综合素质高是不争的事实,因为真正有能力的孩子在任何制度与条件下都有能力在特定的范围内脱颖而出。
更何况高分者进入了教育条件更好的大学,若干年后,彼此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所不同者,我们的教育把绝大多数孩子的学习兴趣与创造力全给磨灭了。
个别地方大学的学生经过个人的努力或者有某个方面的天赋,只是由于短腿致使没能获得进入重点大学的高分,可能日后超 过重点大学的学生,然而这样的学生实在是凤毛麟角,有多少呢?这回大胆用一次百分比:最多1%,换句话说,百里挑
一。
以1%的优秀企图说明一般性肯定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人才问题上根本的错误不在于用人单位是否应该放弃等级观念,事实上你也不可能以个别事例说服用人单位撤掉“地方大学毕业生不得入内”的招牌。
你的个别事例解决不了99%的问题,相反地,还给用人单位提供了口实:“瞧,我们没有歧视地方大学,真正优秀者不是一样‘混’得很好?”社会是多元化的,高校也是多层次的,理论上讲,社会多元化结构与高校多层次结构应该是相匹配的,可悲的是我们的社会有点病态了,把人简单地分成了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事实是不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互是交叉的,即使是脑力劳动者也应该是多层次、多元化的。
这不是企业的问题,而是制度设计者的问题。
如果不从制度层面上作出调整,崇洋媚外、崇拜重点的现状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
就说这高等教育评估吧,尽管地方大学与重点大学的培养目标有很大差别,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等等不一而足, 但评估的标准似乎没有什么差别。
在课程设计上也是这样,按理说,地方大学与重点大学很多课程的目标与重点是有差别的,可实际有什么差别?基本没有。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精品课程”,除了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是分层次进行的,普通院校中无论是地方高校还是重点高校有差别吗?曾经有一个教育部门的领导说过这样的话“:省精品课程可以考虑地方大学,但国家精品课程主要考虑重点大学。
”这句话从逻辑上就错了,既然国家精品课程只针对重点大学,按照当初的设想,精品课程是要辐射其他高校的,那么重点大学的精品课程辐射什么样的高校?地方还是重点?如果是重点,那就叫重点大学精品课程建设好了,如果包括地方,可地方大学的培养体系、目标、方案与重点大学是不同的,这不是自相矛盾么? 说千道万,所有问题的症结都集中在制度设计上,只有先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制度往往不是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设计,而是个别人拍拍脑袋就决定了。
难道拍脑袋的人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u/gfcao)
3 >>>本期关键词:制度 图片来源:/ 人情社会与制度选择 姻马亮 制度选择的问题实在是涉及方方面面,我的日常观察和学术训练告诉我,中国作为关系取向的人情社会,在治理制度的许多方面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以美国、英国等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差异明显,而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领域的表现较为明显。
举个例子。
有一次去美国某大学开会,在那里攻读公共管理博士的华人学生就告诉我,他们从student转为candidate(攻读学位者)前需要通过三门考试,一门是各门课程的综合考查,闭卷限时完成;另外两门则由导师和本专业领域的专家出题,开卷限时完成。
显然,为了公平起见,老师在评阅学生试卷时应该盲审,否则自己指导的学生就可能获得不当之利,在起点上不公平。
但实际上导师为自己的学生出题时并不会徇私,而是会非常严格地对学生进行考查,如果不合格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学生“放倒”。
两门考试后进行选题答辩(proposaldefense),通过这些考查后就成为candidate,可以考虑完成学位论文了。
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由学生的导师担任,成员则由学生根据所在领域的研究状况提名专家,然后由导师确认。
所以学位答辩委员会几乎是清一色的“亲友团”,一般认为不会为难学生。
他们也没有国内越来越重视的盲审,谁审谁的论文都是一清二楚。
这种制度安排显然是建立在充分的互信基础之上的,否则 如果对任何一方不信任,都无法建立这样一种制度。
另外,导师和学生的声誉机制也发挥重要作用,如果导师让学生滥竽充数,那么传出去影响肯定不好。
反之,如果学生舞弊,这样一个污点一旦被发现,则名誉扫地,甚至会毁了一世清名,有时候连学位也会被追回。
由此看来,中国制度的基础就是对人的不信任,哪怕对教授、博士生也不能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总会钻营取巧,所以在论文答辩以后还要进行盲审,因为答辩的老师都是“托”,他们可能包庇,所以要再次核验。
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让博士生们过五关斩六将,有时候到最后一关也可能被放倒。
比较而言,反倒不如通过资格考试,在一两年内告诉你,你可能不适合攻读博士和进行学术研究,毕竟长痛不如短痛。
看到许多煎熬到6~8年才被告知可能无法拿到学位的学长们,这种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显然是令人生畏的。
最近看到有博文探讨博士生期间是否应该发表论文以及发表多了是否合适的问题,显然也与此有关。
因为大学里里外外都很难找到可以公正评判的人选,那么索性通过“社会评价”来进行,寄希望于学术期刊的评审机制可以为大学鉴别学生的研究能力,与此同时也为大学在排名时通过论文发表而加分提供口实。
但国内学术期刊也落入类似的怪圈难以自拔,更何况为大学分忧。
另一个例子就是高等教育入学资格的选拔。
中国高考制度历来褒贬不
一,褒者认为它公平,一把尺子,为社会流动打开了大门;贬者指责它是应试教育的根源,单纯考查智育,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试点自主招生,但其模式与高考无异,只不过在最后环节会设定一个面试,并据此刷掉许多考生。
针对自主招生的观点也和针对高考一样,有认为它矫枉过正的,也有批评它为权势人士大开方便之门的。
我们也看到发达国家会有高考制度,但学生日常表现的考查也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有时候甚至会成为关键因素。
这种制度安排建立在大学对高中的信任上,即可以将高中老师的记录作为评判依据。
而在中国,高中老师的表现记录通 常是难以令人相信的,即便是大学老师为留学生写的推荐信也很难令人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统一考试的权重、降低日常表现记录的权重,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制度选择。
由此联想到国内大学有关同行评议和科学计量学的争论。
现在大学绩效考核、职称评定等都严重依赖科学计量指标,过度量化的考核被人们认为不利于学术界的良性发展,而年度考核的周期安排也诱发短期主义,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许多大学试点助理教授职位,希望通过跨年综合考核来对教师进行指导。
这显然是受到发达国家高校的启发,即为 新进教师留有一个空间,使其可以通过扎实的研究证明自己的能力,然后为其提供tenure(终身职位)。
但如果评审专家徇私,这种制度就很难持续下去,反而不如科学计量学指标来得客观。
也正因为人情社会难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纯粹客观量化的考核就更容易为人接受。
学术期刊评审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最近看了一些研究,发现同行评议是否匿名对评议结果的影响并不大,启示我们匿名评审并不是绝对有效的,我们的制度改革方向可能是矫枉过正。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在发达国家情境下进行的研究,如果在中国,我想可能结果会发生变化。
所以,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社会就为我们选择了适合其社情民意的制度,这种制度只有站在比较的视角下才能评判其优劣和合适与否。
简单地比较就可以发现,制度选择的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非常明显,而如果忽视了这些情境的决定意义,可能会误导制度改革者的视线,并会导致难以预料的不良影响。
因此,在批评我们的社会制度难以尽如人意的同时,我们需要看到,这是社会情境为我们提供的次优选择,因为最优选择的社会条件尚不具备,除非我们改变这种社会条件,否则我们只能接受它或进行更加艰苦的制度创新。
(/u/mliang) 赵汀阳在《博弈问题的哲学分析》(《读书》,2003年第2期)一文中说: 互相不信任和互相视为坏人的共同知识结果就把人真的变成坏人,把本来不确定的丰富世界变成确定的坏世界———我们不能忽视知识的这种生产力……在生产公正的规则的同时生产出坏的世界,这无论如何是个严重的问题。
在今天这个虽然坏但是远远还不是最坏的现实世界里,人们已经建立了相当好的制度,但还是很容易发现,所有人都想从制度中获得好处(这是制度所以获得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所有人都更想钻制度的空子(这是制度所以获得支持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所以落后国家的腐败和发 制 度 姻武 是 夷山 个 大 筐 达国家如美国的大公司丑闻都不足 为奇。
制度总是被设想为来限制别 人的利益的,而自己时刻准备着成为例外的受益者。
孔子所以提倡仁,无非是希望复杂的人际关系 能变成如同二人关系那样单纯。
博主:赵汀阳这番话,除了“所有人”的表达过于 绝对外,还是很深刻的。
我国很多人有一种“制度迷 信”,一方面,它表现为将制度看成中国所有问题的 总根源,有些人在内心深处甚至觉得,中国的制度不 发展到美国那么“先进”,就没有希望
;另一方面,它 表现为一些人将制度不佳作为自己行为不端的挡箭 牌,例如有人说:我为什么要数据造假?是为了发表 论文,不发表论文就拿不到博士学位。
是“不发表论 文就没有资格答辩”这一制度规定逼着我造假的,我 没有责任,制度有责任。
这样的逻辑居然还能获得
一 定的同情。
于是,制度成了一个大筐,什么东西都可以扔进 去。
为什么“三农”问题解决不了?制度问题。
为什么 学术不端行为那么猖獗?制度问题。
为什么中国出不 了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制度问题。
反正什么都是制度 问题,就是“我”没有问题“,我”没有责任。
不是制度不重要,但是不能迷信制度。
我在博文
《处理超越性问题的三种方式》(http: ///m/user_content.aspx?
id=44243) 中曾说: 美国著名媒体批评者、社会学家、学者和作家 Herbert
I.Schille(r1919~2000)1973年在《心智管理 者》(TheMindManagers)一书中说:“人性被看成是 什么样的,最终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因为 人类不得不那样行事,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被期 望着那样行事。
”他的意思是,如果认为人性恶,这
一 看法会影响人的行为,不是因为人必然做坏事,而是 因为“人性恶”的判断好像就期望人们去做坏事。
反 之亦然。
赵汀阳所说的“互相不信任和互相视为坏人的 共同知识结果就把人真的变成坏人”,与
Schiller的 意思是接近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Schiller的潜台 词是:“人性善”的假设更可取。
那么,赵汀阳最后也 回到了认为“人性善”的孔子这里,也就不奇怪了。
我 猜想,2000多年前的孔子,还没有复杂到“希望复杂 的人际关系能变成如同二人关系那样单纯”那种程 度。
但是,赵汀阳对“仁”的这一别解倒也很有意思。
(/u/Wuyishan) 制 度 与 美 德 姻
胡 哪 荣桂 个 更 重 要 在谈论学术不端事件和中国科技界的种种问题时,人们常说一些科学家不讲道德或没有起码的道德底线,但我时常在想,到底什么重要?是美德,还是制度? 科学家必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是大家的期望。
因为大家都认为科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纯粹的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每个科学家都应该如此,即使不是,也应该学习变成这样的人。
我们国家还一直宣扬科学家群体是有美德或讲道德之类,具有高尚风格,注重奉献的人。
但这些所谓的美德是非常不保险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科学家都有高尚的道德、都是活的圣人贤人等等,也不是所有的人天生就愿意做高尚的人,做有美德的人。
科学家更多的是普通人,更多的是经受不了各种诱惑的普通人。
而更为重要的是,讲美德只可以让有美德的人当好人,做好事,做不违背道德的事,那些没有道德,不讲道德的人是不受这些所谓的道德约束的。
所以制度应该比宣扬美德更靠谱,制度可以让那些不想当好人、做有道德的人 变得有德一些,也可以让那 些可做好人也可能做恶人的人弃恶扬善做好 人、做有道德的人。
即制度可以让更多的人有 德。
若人心不向善,人们的行为一再触犯道德 底线,那一定是制度出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只能从制度入手。
当一个科学的、刚性的、不因人而异不徇私 的制度建立起来时,讲道德懂道德的人就会多 起来。
而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社会,总要他人讲 美德、讲道德、讲仁义等等,都是一
件很可笑的 事。
故窃以为制度,不是口中说说而已的制度, 是当今中国社会最为需要的。
有了好的制度,美 德自然会来到我们身边,有了好的制度中国才 会和谐。
(/u/Ecosinic) 如何划分制度的责任与人的责任 姻金拓 事实上
,对于中国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比其他有科学研究这回事的国家严重恐怕没有太多的争论。
谈到原因,应该强调制度的原因还是人的原因却有相反的意见。
我更强调制度的原因,理由如下: 1)在中国揭露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的风险大于实践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的风险。
注意,不是说揭露方一定不成功,而是说揭露方要冒着更大的风险,付出更大的精力,却面对几率更小的成功。
新语丝上揭露过的有根据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中被处理的是极少数,敢实名来揭露的更少。
制度在为哪一方背书一目了然。
2)不错,坏制度下杀人放火仍然绝对是个人的犯罪。
但是一个社会,其犯罪率大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大于同一国家的其他时代,这个“大于”的责任便在制度。
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参考消息》上登过一则消息,一天晚上纽约市停电15分钟,其间偷盗、强奸犯罪活动剧增。
这15分钟之内和之外生活在纽约的人们没有变,但是光明和黑暗下的犯罪率截然不同。
我国当下的学术界便是这样。
不能拿坏制度下个人必须对自己的杀人放火负责来转移坏制度造成杀人放火的比例增高的责任。
3)前段时间网上有人统计过官员和非官 员的犯罪率分别为1/200和1/400,官员高于非官员。
官员犯罪率高说明官员的选拔上负筛选的成分大,而一个社会对于官员的负筛选成分大,一定是制度出了问题。
对于学者的负筛选成分大也是一样的。
4)不错,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也是人干的,说到底还是人成为决定因素。
问题恰恰在这里,即“人”当中包括了握有改变或维护制度的权力的人们,及完全没有权利染指制度的人们。
我们在讨论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时,其实质正是追究握有改变制度权力的人们还是不握有这个权力的人们,谁更该对中国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负责。
我们说“制度更应该强调” 时正是说给有改变制度权力的人们听的。
我们希望他们不但能够听到制度的弊端,而且能意识到更多的人们也已经了解了制度的弊端。
5)也许,我们的讨论与混到有权力改善制度的位置并改善之相比实在是空谈。
但是,混到一定的位置而且不改初衷的难度,未见得小于鼓励已经混到那样的位置的人们改变初衷。
况且,无论是为改变之而混上去还是混上去才想改变之,意识到更多的人希望改变都是必要的。
我们众人在希望这个层次上尚且语无伦次应该不是一件好事。
话说到这份儿上,应该清楚了吧?(/u/jintuo) “个别说明不了一般”vs制度设计 姻曹广福 这是个富有争议的话题,我认为现在由一种观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不赞成门第观念,特别是很多用人单位招聘人才的基本条件中非“211”“、985”高校不要,有些单位干脆高挂媚外牌子:“非海龟不要”,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愚蠢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起了非“211”、“985”高校毕业生的众怒,二是的确有可能错过了出身“卑微”但真正优秀的人才。
我曾经对一个领导说:“你们自己培养的优秀生都不想要,你还指望谁要你的学生?”你可以在实际操作时侧重于“211”、“985”高校,例如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出身好一点的人才,这么做大家还是能理解的,因为“211”、“985”大学与地方大学除了生源上的差别,师资的差别也是不容忽视的,而这种差别决定了学生的学术素养与眼界的差别。
见过一所地方大学的招聘条件,应聘者必须是重点大学具有国家重点学科专业的博士或者海外博士。
这个条件中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误认为只要是海外的博士就是优秀者。
我见过一些海龟,有大牛,也有平庸者,有些用人单位既然把国内人才分成了三六九等,为什么不把海龟也分 一分呢?崇洋媚外心理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用人单位在聘人问题 上的确不应该有门第等级观念,说得好听点是门第观念,说得难听一点是狗眼看人低。
话说回头,出身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综合素质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虽然我们一贯抨击今天的中小学教育,把聪明孩子教笨了,但即使是今天这样的教育体制,好学生与差学生还是能区分出来的,你高兴听或者不高兴听都否认不了这个事实。
可能有人会质疑什么是好学生什么是差学生,这也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姑且以综合素质论吧。
也许有人会以高分低能反驳我,高分低能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同样的教育体制与条件下,个别或许有例外,整体而言,高分者比低分者综合素质高是不争的事实,因为真正有能力的孩子在任何制度与条件下都有能力在特定的范围内脱颖而出。
更何况高分者进入了教育条件更好的大学,若干年后,彼此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所不同者,我们的教育把绝大多数孩子的学习兴趣与创造力全给磨灭了。
个别地方大学的学生经过个人的努力或者有某个方面的天赋,只是由于短腿致使没能获得进入重点大学的高分,可能日后超 过重点大学的学生,然而这样的学生实在是凤毛麟角,有多少呢?这回大胆用一次百分比:最多1%,换句话说,百里挑
一。
以1%的优秀企图说明一般性肯定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人才问题上根本的错误不在于用人单位是否应该放弃等级观念,事实上你也不可能以个别事例说服用人单位撤掉“地方大学毕业生不得入内”的招牌。
你的个别事例解决不了99%的问题,相反地,还给用人单位提供了口实:“瞧,我们没有歧视地方大学,真正优秀者不是一样‘混’得很好?”社会是多元化的,高校也是多层次的,理论上讲,社会多元化结构与高校多层次结构应该是相匹配的,可悲的是我们的社会有点病态了,把人简单地分成了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事实是不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互是交叉的,即使是脑力劳动者也应该是多层次、多元化的。
这不是企业的问题,而是制度设计者的问题。
如果不从制度层面上作出调整,崇洋媚外、崇拜重点的现状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
就说这高等教育评估吧,尽管地方大学与重点大学的培养目标有很大差别,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等等不一而足, 但评估的标准似乎没有什么差别。
在课程设计上也是这样,按理说,地方大学与重点大学很多课程的目标与重点是有差别的,可实际有什么差别?基本没有。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精品课程”,除了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是分层次进行的,普通院校中无论是地方高校还是重点高校有差别吗?曾经有一个教育部门的领导说过这样的话“:省精品课程可以考虑地方大学,但国家精品课程主要考虑重点大学。
”这句话从逻辑上就错了,既然国家精品课程只针对重点大学,按照当初的设想,精品课程是要辐射其他高校的,那么重点大学的精品课程辐射什么样的高校?地方还是重点?如果是重点,那就叫重点大学精品课程建设好了,如果包括地方,可地方大学的培养体系、目标、方案与重点大学是不同的,这不是自相矛盾么? 说千道万,所有问题的症结都集中在制度设计上,只有先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制度往往不是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设计,而是个别人拍拍脑袋就决定了。
难道拍脑袋的人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u/gfcao)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