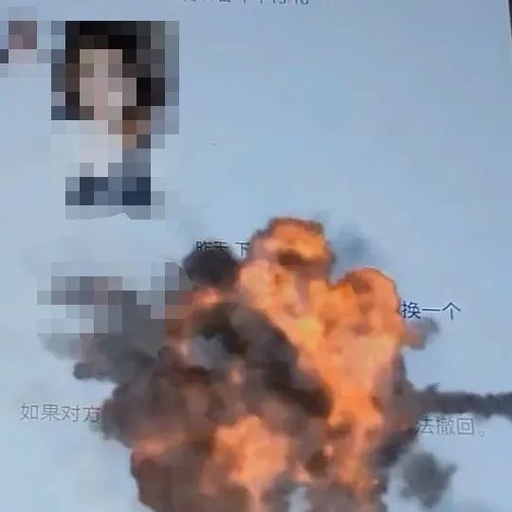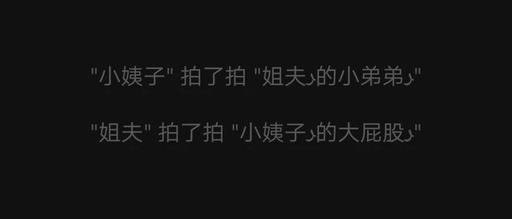刊采由木铎蕴雅颂
第五版《采风周刊》第283期总编室主办
【手记】
“我本来没想讲那么多,但不讲这些,你不知道老干部处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
”记者一直记得张伟说这句话时的神情。
为了照顾父亲,他专门去买了北医三院出版的《渐冻人家庭护理手册》和美国著名作家米奇·阿尔博姆的著作《相约星期二》。
一年零八个月,眼看着父亲从最初的强势到接受现实、到最后的无能为力,如果没有老干部处的陪伴和支持,张伟不知道自己和家人将如何安抚被疾病折磨的父亲。
下一个人生目标 还有刚与病魔擦肩而过的高嘉生,我在“金色园地”里看到他写的《我的下一个人生目标》一文:“一场大病差点把我彻底毁灭,多亏我的领导、同事们、朋友们和我的同学们以及关心我爱护我的家人、亲戚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刻给了我无穷无尽的战胜病魔的勇气和力量。
我的下一个人生目标就是安全度过五年生存期,为艰难迎接每一天、每一月和每一年的到来而继续努力!” 人生如同一场电影,既有“人在旅途”的困惑,也有相遇“心灵捕手”的喜悦,更有“金色池塘”的梦想,最终在落幕时完成自己的“遗愿清单”。
一个能够让人思考生命价值的工作绝对是一份好工作,一个对生命有着清晰认识,不断焕发你对生活的热爱,并能陪伴你走到人生终点的组织,绝对是你值得托付终生的事业归属所在,记者为上海高院老干部处团队而骄傲! 当你老了 ——记“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上海高院老干部处 本报记者严剑漪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取暖回忆青春。
”当我们老了,我们会走向哪里? 心灵捕手 刘永深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老干部处做副处长已经一年多了,和其他同事相比,他还是老干部处的一名“新兵”。
来之前,他以为这里的工作就是跑跑腿,没想到里面还有那么多“道道儿”。
一位老同志打来电话,他的退休金没收到。
其实这事儿完全可以直接去问社保局,但涉及老同志切身利益的事得马上办,刘永深不敢懈怠,立即联系相关科室问清情况,然后反馈给老同志。
一位老同志的记性不好,搞不清自己有没有交党费,刘永深提醒自己不能直言“你没交,过来交”,而是委婉地安慰电话里的人:“别急,别急,我们再找找。
”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次拨通老同志的电话,笑着问:“想起来了吗?” 老了,就像孩子。
组织,就像家。
随时掌握情况,随时发生状况,刘永深觉得自己就像时刻待命的战士,号角一吹,他就一跃而出。
处里一共7个人,工作时间最长的是田苏香,近20年一直任劳任怨;性格温顺的赵红嗓音甜美,常常组织老同志一起去歌舞沙龙;张为人专门负责离休退休老干部联合党支部,工作有条不紊;贾蕾有着一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总是默默地付出;张锐做事沉稳,信息录入、数据管理样样拿手。
不过,刘永深最佩服的还是老处长丁美玲,有人曾这样说:“如果让丁美玲去种棉花,她也会种得很有意义。
”丁美玲还真种过棉花。
1977年,年纪轻轻的她在崇明干校给学员讲授如何种植棉花,坐在下面的学员听得津津有味,都以为这小丫头出生于农村。
“我很安于现状,给我什么工作,我就认认真真去做。
我又不安于现状,给我的工作,我总是尽力去把它做得更好。
”丁美玲很了解自己。
1978年,丁美玲来到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先在民庭办案2年,然后调到经济庭7年,接着又在办公室工作了1年,最后来到立案庭,负责立案信访接待。
1998年她正式调往上海高院立案庭,2012年她来到高院老干部处。
从民商事条线到立案接待窗口,丁美玲接触最多的就是人,与人打交道、为人服务,让她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调到老干部处后,丁美玲可高兴了,这回是为自己年轻时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们服务。
第一次与全体老干部见面,丁美玲便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和宅电号码告诉了所有在场的人:“你们如果有事,无论事情大小,无论时间早晚,都可以联系我。
”老同志们顿时乐开了,坐在台下的李海庆赶紧记下丁美玲的电话。
李海庆80多岁,解放前在厂里当学徒,1953年被选拔到法院,1960年调至上海高院办公室研究组,成为“上海法院外事接待第一人”,1993年退休。
“这样好,彼此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李海庆很欣赏丁美玲的工作风格。
然而,要把所有的细节都做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老干部处7人,面对的是4个支部260余名老同志,这些老同志平均年龄71.5岁,75岁以上老人近40%,高龄、独居、生活不能自理、家庭负担沉重约占四分之
一。
丁美玲带着团队不停地走访,春节、高温、生病、特困,定期组织老干部政策和健康讲座,每周召开一次处务会,沟通各支部情况。
处里的一套“上海法院老干部工作管理系统”也在不断完善,人员管理、工作管理、短信平台、文件管理、查询统计,功能样样具备,所有老同志的工作简历、家属情况、历年体检、年龄结构、队伍分析和支部建设情况,在电脑里一目了然。
一次,外出搞组织活动,天空突然下雨,老同志们淋湿了,丁美玲赶紧和同事联系了一家餐饮店,煮上一大锅姜汤给大家喝。
老同志家里闹矛盾了,丁美玲和田苏香仔细商量,然后由田苏香和支部委员通过电话和上门方式多次做工作;老同志提出想住养老院,老干部处马上热心推荐,等到入住了养老院,田苏香不仅自己忙着前去探望,还组织支部委员 们也同去养老院看望。
90多岁的老杨没有收到院里发出 的体检表,急得不行,打电话问老干部处,丁美玲连忙回答“你放心,我们会帮你办好”。
体检当天,她亲自陪着老杨去一个个科室检查,老杨感激不尽。
“法院就像一台机器,每个角落都需要有螺丝钉,虽然可能谁也不会关注那颗螺丝钉,但缺了它不行。
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做好一颗螺丝钉。
”丁美玲说。
但是,做了这些还不够。
金色池塘 李海庆曾是离退休老干部联合支部的书记,当他走进老蔡家中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吃惊。
脸色苍白的老蔡躺在阳台临时搭建的“卧室”里,头发上满是头皮屑。
由于厕所是与邻居共用,儿子在老蔡睡的小床边放了一个雪碧瓶,瓶子上开了一个洞口,然后插上一根管子连着老蔡,方便他如厕时使用。
老蔡每天只有两顿饭,早饭是儿子在外面买的点心,午饭是儿子叫来的外卖,晚饭就没有了。
这就是曾经相貌堂堂、潇洒帅气的老蔡吗?李海庆一阵心酸。
老蔡曾在解放前做过地下党,进入法院后担任刑庭副庭长,如今妻子去世,留下两儿一女。
小儿子离婚了,老蔡把房间让给儿子,自己睡在阳台。
大儿子失业,儿媳也没工作,老蔡靠自己一人的退休工资养活着孩子们,包括第三代。
女儿结婚了,偶尔回来看望一下老父亲。
看到老蔡晚年生活如此凄凉,李海庆立即找到丁美玲。
丁美玲和老干部处的同事们多次看望老蔡,为他带来一些生活必须品,并为老蔡联系了几家敬老院,但老蔡拒绝了。
去敬老院得花钱,他不愿多花一分钱在自己身上。
2013年老蔡病重,送往护理院后去世。
“人老了以后,关键是感到寂寞。
有子女在身边孝敬的就幸福,没有子女关爱的就寂寞,这是最痛苦的。
”李海庆感慨地说。
同样是离休干部,老贾就幸运多了,女儿对他寸步不离,除了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弄好吃的,还为他买了把按摩椅,可爱的外孙教他怎么使用“新式武器”,子女们随叫随到,老贾引以为豪。
“人活着,不仅仅是活,而是要活得开心,活得有价值。
”丁美玲思考着。
很快,老同志们发现,以往老干部处会为满“十”周岁的60、70、80、90岁老同志集体过生日,但90岁老人往往因为行动不便而无法参加。
现在,老干部处亲自上门为90岁以上老人祝寿,而且95岁以后,老人可以年年享受这份登门祝寿的喜悦。
2012年7月15日上午,丁美玲和退休第二支部的支部书记应书益一行人,拿着蛋糕笑呵呵地出现在蒋浚泉家门前,这是丁美玲上任后第一次给90岁老人上门祝寿,她特意挑了上午登门,因为大多数老人一般都有睡午觉的习惯。
蒋浚泉开心极了,曾在法院办公室负责司法统计的他,看到法院人就像看到自己的亲人:“啊呀,天气那么热,你们 还记得我的生日,真是太高兴了!”蒋浚泉的快乐也感染了身边的女 儿,女儿忙里忙外地给丁美玲等人端上家里的点心。
生日贺卡、对联、拍照片、吃蛋糕,虽然屋内有些狭小,但欢乐的气氛充满了整个空间。
“谢谢组织关心啊,等我100岁时请你们再来!”蒋浚泉的一句话让所有人笑开了怀。
钱鸿祥也体验到了这种幸福。
2014年,老干部处专门给95岁的他去祝寿。
钱鸿祥曾在法院做水电工,为人善良热情,无论谁家有困难,只要是和水电有关,他二话不说赶去修理,退休后也常常助人为乐。
“退休以后,还有组织时刻在关心,这对我们个人和家庭的意义不一样。
”应书益记得,有一次他和丁美玲去医院给一位95岁的老同志祝寿,护士们被感动了,说了一句“这样的单位从来没有见过”,然后主动把会议室让给老同志们祝寿用。
“老干部处能够做到对老领导、老同志一视同仁,非常好!”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上海高院副院长的李国光很欣赏老干部处的做法,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院长曾是北大毕业的高才生,历经四级法院的磨炼,度过了整整42年的法律生涯,身为中国首批大法官的他一直平易近人。
“我最喜欢你给我带的点心,好吃得不得了!”今年99岁高龄的翁老是目前退休老干部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每次看到老干部处来人,她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丁美玲总会带些食堂做的点心给她,陪她聊聊天。
“对老同志来说,我们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要和他们有情感上的共鸣和交流。
”丁美玲这样要求团队。
人在旅途 2014年12月24日,盼望已久的上海高院老干部活动中心终于成立。
很快,丰富多彩的兴趣班开始了,电脑、太极拳、合唱团、摄影班、微信讲座,老同志们的走动越来越多。
90岁高龄的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上海高院原院长华联奎也兴致勃勃地在老师指导下开通了微信,加入了上海高院老干部的“高老微”微信群。
部局级干部和一般干部在群里畅所欲言,从富有哲理的生活启示到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从赏心悦目的美景照片到忍俊不禁的笑话视频,细心的老干部处7人“潜水”于其中,不时地“冒个泡”,发一些健康养生知识和生活小技能,受到群友“热捧”。
有时候,老干部处还在群里回应老干部们提出的一些疑惑。
没多久,“金色园地”APP也上线了。
老同志们可以通过手机每天阅读到法院的最新消息、关怀动态、学习修为、乐活交流和流金岁月等栏目,《致病中的范书记》《致好友太兴》《致年子》《致仁抗老弟》《致秋的季节》,一篇篇感人肺腑的美文也在出炉——“2016年1月15日,是范祖祥书记73周岁生日。
想当初,农家乐欢声笑语;想当初学习班心语恳谈……愿祖祥书记战胜病魔,早日康复,幸 福的晚年生活一起分享。
”2015年12月24日,退休二支部的 老同志们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学习,不知是谁冒出一句话:“今天好像是活动中心成立一周年嘛。
” “对哦,要庆贺一下啊!”上海高院原副院长姚赓麟幽默地接上一句话,大家哈哈一笑。
15分钟后,工作人员送来了一块块小蛋糕,原来,丁美玲悄悄数了一下参会人数,安排人去买蛋糕了,考虑到有些老人患糖尿病,她还专门让人买了一部分咸味的点心,老同志一片惊喜。
“刚退休的人工作放下了,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了,这时候的他(她)完全释放自我,5到10年内不大来找组织。
65岁到70岁的人,开始出现衰老迹象,这时候他(她)慢慢回归原来的朋友圈。
75岁以后,生活上有困难了,他(她)开始依靠组织。
80岁以上,完全依赖组织。
”这是丁美玲做了处长后的体会。
的确,能够在退休以后快乐地享受生活,活出自己的价值,尽量多的为组织添光增彩,尽量少的麻烦组织,这是很多老干部的心愿。
退休二支部的厉民一曾是上海高院经济庭的一名资深法官,退休以后,他在自己居住地所在的街镇担任老年维权服务总站首席法律服务者。
从法律咨询到诉讼须知,从涉诉调解到指导法律服务志愿者,老厉的专业和热情在街镇远近闻名。
一次,在街道组织的现场法律咨询活动中,有位外来清洁打工者神情落寞地坐在老厉对面,原来他被单位无故解除劳动关系,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
老厉听出了对方心中的怨气,马上引导他通过仲裁方式寻求法律上的经济补偿。
“一个人对人民的服务,不一定要站在大会上讲演或是作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随时随地,点点滴滴地把自己知道的、想到的告诉大家,无形中就是替国家播种、垦植。
”老厉非常喜欢傅雷的这段话。
像厉民一这样的老干部很多,他们退休后,有的自发的在社区为老百姓服务,有的协助法院做好诉前调解,有的帮忙监察室做好审务督查工作,还有的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以讲课形式与更多年轻人分享。
“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老干部处的工作就是做好服务与保障,发挥老同志们的特长,让他们更好地为社会增添正能量。
”丁美玲说,也正因为此,她要求团队的人在保障老干部及家属权益方面不能有一点闪失。
离休干部老王生前留有一笔数额不小的存款,熟悉老王家庭情况的张为人处理老王后事时特别谨慎,他知道老王曾经领养过一个女儿,后来养女与后母关系不佳,一气之下离家而走。
“从法律上讲,养女也有继承权利的,她不签字,我这里无法发抚恤金。
”张为人委婉地向老王后妻解释法律规定。
“已经多年没有联系她了,怎么办?”王妻问道。
看到王妻有所松动,张为人赶紧翻开档案找到养女的联系电话,然后给了王妻。
接到后母电话的养女连忙赶到老王 上海高院老干部处集体合影,左起依次为贾蕾、赵红、田苏香、丁美玲、刘永深、张为人、张锐。
孟招祥摄 的遗体告别仪式现场,想起养父曾经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养女深感内疚,与后母也冰释前嫌。
到法院领取抚恤金当天,养女和后母在法院拍了张合影,养女轻轻对后母说:“阿姨,以后我们要多来往来往。
” 遗愿清单 在老干部处工作的人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那是其他部门所不会遇见的,那就是——面对死亡。
“有时候家属突然打电话来说,人已经到最后了,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过去,能见最后一面就见,不能见最后一面,也要去家中慰问,问一问家属有什么需求。
”刘永深说。
抚恤金如何发放、讣告生平内容怎么写,甚至花圈怎么摆放、挽联顺序如何,一切都是细节活儿。
然而,这还不是最揪心的,最难做的是面临死亡时如何劝慰患病的老同志。
很多人都是大限将至时,才第一次认真思考死亡。
张伟永远也忘不了,在父亲生命最后的一年零八个月里,老干部处给予父亲和他的支持。
老张曾担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经济庭庭长、副院长,后调至上海高院担任经济庭庭长、审委会委员、副巡视员,然后退休。
在张伟的童年记忆里,父亲从早到晚地加班,有时候还是华政的指导老师,平日里只要弄堂里哪家发生纠纷,必然会找父亲来主持公道。
善良、敬业、坚强,这是父亲留给张伟的印象,他从未见过父亲流眼泪。
2013年,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张与妻子度过了金婚纪念日,不久,老张发现自己的声音变哑了,人也在渐渐消瘦。
张伟陪着父亲前往中山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张伟一个噩耗:“你父亲得的是运动元神经,俗称渐冻症,所有神经技能会一一丧失,最后呼吸衰竭而死。
这个病是不可逆的,无药可救。
”医生给张伟推荐了一个可以延缓病情发展的药。
张伟懵了,他强忍着悲痛和妹妹商量,最后决定暂时不告诉父亲病情,而是购买药物以延缓父亲病情的发展。
细心的他给药物的包装和说明书做了“手脚”,避免父亲得知真相。
然而,老张还是发现了。
一次,他无意间听到医生在走廊上的对话,医生说他的病实际就是“死刑缓刑”。
老张大怒,一下子吵到了医务处,医患矛盾骤升,医院只得打电话找到了老干部处。
丁美玲很理解老张的心情,在老张之前,已经有一位老干部因为相同的病症而去世。
听着老张喋喋不休的“控诉”,丁美玲知道自己说什么劝慰的话都是无用的。
她“扳”起了脸“:老张,医生在走道上随意议论病人病情是不对,但他说的是实情。
一个人的生命长度是老天定的,但生命的宽度则是自己定的,开开心心是一天,焦虑不安也是一天,老张,希望你加大宽度,快乐过好每一天。
” 丁美玲的“当头一棒”喝醒了老张。
过了一段时间,丁美玲再去看望老张,老张拿着台历上自己写的字给她看:“无论碰到什么困难,我希望不屈不挠,让每天都充满希望和愉快,与患难为友,绝望也能锻炼我,摆正长度与宽度的关系,过好每一天。
” 2014年5月,老张因脚肿住进医院,此时的他伴有强烈的咳嗽却无法咳出痰液。
一个星期后,生命体征降到最低,医院开出病危通知书,并询问家属是否需要切开气管。
切还是不切?张伟陷入痛苦之中。
不切,父亲有可能会失去生命;切开,以后的生活质量就一落千丈。
最后,张伟签字同意切开气管。
抢救回来的老张躺在ICU里,张伟通过写字板和父亲交流,老张在纸上慢慢写:“我还想要活下去,你帮我多活两年。
”张伟强忍泪水写到:“你放心,时间长着呢。
” 然而,情况总是超乎家人的想象,老张的心脏不断出现异常,病危通知书一张接着一张,每次丁美玲都会及时赶来,张伟后来才知道,当时丁美玲的父亲也在重病住院。
老张的脾气越来越焦躁,一次,他吵着要搬出ICU,一怒之下把写字板扔在张伟身上,张伟低头一看纸条,上面写着:“我再也不相信医院了!” 无奈的张伟只得打电话叫来丁美玲。
当丁美玲一走进ICU时,老张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不能哭,你再哭我就走了。
”丁美玲一边说一边打手势,“把眼泪忍住,不哭了。
你不能激动,你一激动心脏病要加重,放松,笑一笑!” 老张听话地抿紧嘴唇,强忍眼泪,又点头又摇头。
从没见过父亲哭过的张伟心酸不已,这就是曾经坚不可摧的父亲啊! “第
一,你要配合治疗,你想换病房,大家都理解,目前没有条件,我们正在争取。
再等两天,你相信我吗?”丁美玲问。
老张使劲儿点头,情绪一下子平静下来。
一年零八个月,这是老张人生中难熬的一段岁月,也是老张家人悲伤心碎的一段日子。
“回去问你妈妈好,让她照顾好自己,这里有我们。
”丁美玲不止一次地提醒张伟。
最后的日子里,老张常常眼神定定地望着天花板,一望就是一两个小时,张伟和他说话,他也没有反应。
只有当丁美玲来病房看望他时,老张的嘴角才会努力上扬一下,有时候是嘴唇抿一下。
2016年1月6日,老张于凌晨5时离开人世,离世前,张伟在父亲的耳边轻轻说:“爸爸,你安安心心走吧,我每年会来看你的。
你有什么告诉我,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 1月8日,丁美玲参加完老张的遗体告别仪式,错过了前往重症监护室探望自己父亲的时间,第二天,老父亲去世。
“父亲这里,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虽然我没有看到他最后一眼。
”丁美玲说,“我现在对人生看得比较透,人的生命很珍贵,但是要有尊严,有尊严地活着,有尊严地走。
” 2016年12月23日,上海高院老干部处被授予“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这是一次各行各业老干部工作的评比,是上海法院前所未有的殊荣,“高老微”微信群兴奋不已,大家交口称赞老干部处“当之无愧”。
丁美玲作为先进集体代表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表彰大会。
2016年8月,丁美玲升为上海高院副巡视员,再过1年,她也即将退休。
2017年3月,老干部处的田苏香退休,开始回家带孙子。
2017年1月,39岁的王薇加入老干部处,成为处里的又一位新人。
“在法院工作的人,一生中待得最久的部门就是老干部处,退休以后都归老干部处。
”丁美玲的话萦绕在记者的耳旁。
责任编辑陈冰新闻热线(010)67550710电子信箱chenbing@ 欢迎广大读者提供人物报道稿件或线索
”记者一直记得张伟说这句话时的神情。
为了照顾父亲,他专门去买了北医三院出版的《渐冻人家庭护理手册》和美国著名作家米奇·阿尔博姆的著作《相约星期二》。
一年零八个月,眼看着父亲从最初的强势到接受现实、到最后的无能为力,如果没有老干部处的陪伴和支持,张伟不知道自己和家人将如何安抚被疾病折磨的父亲。
下一个人生目标 还有刚与病魔擦肩而过的高嘉生,我在“金色园地”里看到他写的《我的下一个人生目标》一文:“一场大病差点把我彻底毁灭,多亏我的领导、同事们、朋友们和我的同学们以及关心我爱护我的家人、亲戚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刻给了我无穷无尽的战胜病魔的勇气和力量。
我的下一个人生目标就是安全度过五年生存期,为艰难迎接每一天、每一月和每一年的到来而继续努力!” 人生如同一场电影,既有“人在旅途”的困惑,也有相遇“心灵捕手”的喜悦,更有“金色池塘”的梦想,最终在落幕时完成自己的“遗愿清单”。
一个能够让人思考生命价值的工作绝对是一份好工作,一个对生命有着清晰认识,不断焕发你对生活的热爱,并能陪伴你走到人生终点的组织,绝对是你值得托付终生的事业归属所在,记者为上海高院老干部处团队而骄傲! 当你老了 ——记“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上海高院老干部处 本报记者严剑漪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取暖回忆青春。
”当我们老了,我们会走向哪里? 心灵捕手 刘永深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老干部处做副处长已经一年多了,和其他同事相比,他还是老干部处的一名“新兵”。
来之前,他以为这里的工作就是跑跑腿,没想到里面还有那么多“道道儿”。
一位老同志打来电话,他的退休金没收到。
其实这事儿完全可以直接去问社保局,但涉及老同志切身利益的事得马上办,刘永深不敢懈怠,立即联系相关科室问清情况,然后反馈给老同志。
一位老同志的记性不好,搞不清自己有没有交党费,刘永深提醒自己不能直言“你没交,过来交”,而是委婉地安慰电话里的人:“别急,别急,我们再找找。
”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次拨通老同志的电话,笑着问:“想起来了吗?” 老了,就像孩子。
组织,就像家。
随时掌握情况,随时发生状况,刘永深觉得自己就像时刻待命的战士,号角一吹,他就一跃而出。
处里一共7个人,工作时间最长的是田苏香,近20年一直任劳任怨;性格温顺的赵红嗓音甜美,常常组织老同志一起去歌舞沙龙;张为人专门负责离休退休老干部联合党支部,工作有条不紊;贾蕾有着一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总是默默地付出;张锐做事沉稳,信息录入、数据管理样样拿手。
不过,刘永深最佩服的还是老处长丁美玲,有人曾这样说:“如果让丁美玲去种棉花,她也会种得很有意义。
”丁美玲还真种过棉花。
1977年,年纪轻轻的她在崇明干校给学员讲授如何种植棉花,坐在下面的学员听得津津有味,都以为这小丫头出生于农村。
“我很安于现状,给我什么工作,我就认认真真去做。
我又不安于现状,给我的工作,我总是尽力去把它做得更好。
”丁美玲很了解自己。
1978年,丁美玲来到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先在民庭办案2年,然后调到经济庭7年,接着又在办公室工作了1年,最后来到立案庭,负责立案信访接待。
1998年她正式调往上海高院立案庭,2012年她来到高院老干部处。
从民商事条线到立案接待窗口,丁美玲接触最多的就是人,与人打交道、为人服务,让她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调到老干部处后,丁美玲可高兴了,这回是为自己年轻时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们服务。
第一次与全体老干部见面,丁美玲便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和宅电号码告诉了所有在场的人:“你们如果有事,无论事情大小,无论时间早晚,都可以联系我。
”老同志们顿时乐开了,坐在台下的李海庆赶紧记下丁美玲的电话。
李海庆80多岁,解放前在厂里当学徒,1953年被选拔到法院,1960年调至上海高院办公室研究组,成为“上海法院外事接待第一人”,1993年退休。
“这样好,彼此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李海庆很欣赏丁美玲的工作风格。
然而,要把所有的细节都做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老干部处7人,面对的是4个支部260余名老同志,这些老同志平均年龄71.5岁,75岁以上老人近40%,高龄、独居、生活不能自理、家庭负担沉重约占四分之
一。
丁美玲带着团队不停地走访,春节、高温、生病、特困,定期组织老干部政策和健康讲座,每周召开一次处务会,沟通各支部情况。
处里的一套“上海法院老干部工作管理系统”也在不断完善,人员管理、工作管理、短信平台、文件管理、查询统计,功能样样具备,所有老同志的工作简历、家属情况、历年体检、年龄结构、队伍分析和支部建设情况,在电脑里一目了然。
一次,外出搞组织活动,天空突然下雨,老同志们淋湿了,丁美玲赶紧和同事联系了一家餐饮店,煮上一大锅姜汤给大家喝。
老同志家里闹矛盾了,丁美玲和田苏香仔细商量,然后由田苏香和支部委员通过电话和上门方式多次做工作;老同志提出想住养老院,老干部处马上热心推荐,等到入住了养老院,田苏香不仅自己忙着前去探望,还组织支部委员 们也同去养老院看望。
90多岁的老杨没有收到院里发出 的体检表,急得不行,打电话问老干部处,丁美玲连忙回答“你放心,我们会帮你办好”。
体检当天,她亲自陪着老杨去一个个科室检查,老杨感激不尽。
“法院就像一台机器,每个角落都需要有螺丝钉,虽然可能谁也不会关注那颗螺丝钉,但缺了它不行。
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做好一颗螺丝钉。
”丁美玲说。
但是,做了这些还不够。
金色池塘 李海庆曾是离退休老干部联合支部的书记,当他走进老蔡家中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吃惊。
脸色苍白的老蔡躺在阳台临时搭建的“卧室”里,头发上满是头皮屑。
由于厕所是与邻居共用,儿子在老蔡睡的小床边放了一个雪碧瓶,瓶子上开了一个洞口,然后插上一根管子连着老蔡,方便他如厕时使用。
老蔡每天只有两顿饭,早饭是儿子在外面买的点心,午饭是儿子叫来的外卖,晚饭就没有了。
这就是曾经相貌堂堂、潇洒帅气的老蔡吗?李海庆一阵心酸。
老蔡曾在解放前做过地下党,进入法院后担任刑庭副庭长,如今妻子去世,留下两儿一女。
小儿子离婚了,老蔡把房间让给儿子,自己睡在阳台。
大儿子失业,儿媳也没工作,老蔡靠自己一人的退休工资养活着孩子们,包括第三代。
女儿结婚了,偶尔回来看望一下老父亲。
看到老蔡晚年生活如此凄凉,李海庆立即找到丁美玲。
丁美玲和老干部处的同事们多次看望老蔡,为他带来一些生活必须品,并为老蔡联系了几家敬老院,但老蔡拒绝了。
去敬老院得花钱,他不愿多花一分钱在自己身上。
2013年老蔡病重,送往护理院后去世。
“人老了以后,关键是感到寂寞。
有子女在身边孝敬的就幸福,没有子女关爱的就寂寞,这是最痛苦的。
”李海庆感慨地说。
同样是离休干部,老贾就幸运多了,女儿对他寸步不离,除了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弄好吃的,还为他买了把按摩椅,可爱的外孙教他怎么使用“新式武器”,子女们随叫随到,老贾引以为豪。
“人活着,不仅仅是活,而是要活得开心,活得有价值。
”丁美玲思考着。
很快,老同志们发现,以往老干部处会为满“十”周岁的60、70、80、90岁老同志集体过生日,但90岁老人往往因为行动不便而无法参加。
现在,老干部处亲自上门为90岁以上老人祝寿,而且95岁以后,老人可以年年享受这份登门祝寿的喜悦。
2012年7月15日上午,丁美玲和退休第二支部的支部书记应书益一行人,拿着蛋糕笑呵呵地出现在蒋浚泉家门前,这是丁美玲上任后第一次给90岁老人上门祝寿,她特意挑了上午登门,因为大多数老人一般都有睡午觉的习惯。
蒋浚泉开心极了,曾在法院办公室负责司法统计的他,看到法院人就像看到自己的亲人:“啊呀,天气那么热,你们 还记得我的生日,真是太高兴了!”蒋浚泉的快乐也感染了身边的女 儿,女儿忙里忙外地给丁美玲等人端上家里的点心。
生日贺卡、对联、拍照片、吃蛋糕,虽然屋内有些狭小,但欢乐的气氛充满了整个空间。
“谢谢组织关心啊,等我100岁时请你们再来!”蒋浚泉的一句话让所有人笑开了怀。
钱鸿祥也体验到了这种幸福。
2014年,老干部处专门给95岁的他去祝寿。
钱鸿祥曾在法院做水电工,为人善良热情,无论谁家有困难,只要是和水电有关,他二话不说赶去修理,退休后也常常助人为乐。
“退休以后,还有组织时刻在关心,这对我们个人和家庭的意义不一样。
”应书益记得,有一次他和丁美玲去医院给一位95岁的老同志祝寿,护士们被感动了,说了一句“这样的单位从来没有见过”,然后主动把会议室让给老同志们祝寿用。
“老干部处能够做到对老领导、老同志一视同仁,非常好!”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上海高院副院长的李国光很欣赏老干部处的做法,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院长曾是北大毕业的高才生,历经四级法院的磨炼,度过了整整42年的法律生涯,身为中国首批大法官的他一直平易近人。
“我最喜欢你给我带的点心,好吃得不得了!”今年99岁高龄的翁老是目前退休老干部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每次看到老干部处来人,她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丁美玲总会带些食堂做的点心给她,陪她聊聊天。
“对老同志来说,我们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要和他们有情感上的共鸣和交流。
”丁美玲这样要求团队。
人在旅途 2014年12月24日,盼望已久的上海高院老干部活动中心终于成立。
很快,丰富多彩的兴趣班开始了,电脑、太极拳、合唱团、摄影班、微信讲座,老同志们的走动越来越多。
90岁高龄的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上海高院原院长华联奎也兴致勃勃地在老师指导下开通了微信,加入了上海高院老干部的“高老微”微信群。
部局级干部和一般干部在群里畅所欲言,从富有哲理的生活启示到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从赏心悦目的美景照片到忍俊不禁的笑话视频,细心的老干部处7人“潜水”于其中,不时地“冒个泡”,发一些健康养生知识和生活小技能,受到群友“热捧”。
有时候,老干部处还在群里回应老干部们提出的一些疑惑。
没多久,“金色园地”APP也上线了。
老同志们可以通过手机每天阅读到法院的最新消息、关怀动态、学习修为、乐活交流和流金岁月等栏目,《致病中的范书记》《致好友太兴》《致年子》《致仁抗老弟》《致秋的季节》,一篇篇感人肺腑的美文也在出炉——“2016年1月15日,是范祖祥书记73周岁生日。
想当初,农家乐欢声笑语;想当初学习班心语恳谈……愿祖祥书记战胜病魔,早日康复,幸 福的晚年生活一起分享。
”2015年12月24日,退休二支部的 老同志们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学习,不知是谁冒出一句话:“今天好像是活动中心成立一周年嘛。
” “对哦,要庆贺一下啊!”上海高院原副院长姚赓麟幽默地接上一句话,大家哈哈一笑。
15分钟后,工作人员送来了一块块小蛋糕,原来,丁美玲悄悄数了一下参会人数,安排人去买蛋糕了,考虑到有些老人患糖尿病,她还专门让人买了一部分咸味的点心,老同志一片惊喜。
“刚退休的人工作放下了,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了,这时候的他(她)完全释放自我,5到10年内不大来找组织。
65岁到70岁的人,开始出现衰老迹象,这时候他(她)慢慢回归原来的朋友圈。
75岁以后,生活上有困难了,他(她)开始依靠组织。
80岁以上,完全依赖组织。
”这是丁美玲做了处长后的体会。
的确,能够在退休以后快乐地享受生活,活出自己的价值,尽量多的为组织添光增彩,尽量少的麻烦组织,这是很多老干部的心愿。
退休二支部的厉民一曾是上海高院经济庭的一名资深法官,退休以后,他在自己居住地所在的街镇担任老年维权服务总站首席法律服务者。
从法律咨询到诉讼须知,从涉诉调解到指导法律服务志愿者,老厉的专业和热情在街镇远近闻名。
一次,在街道组织的现场法律咨询活动中,有位外来清洁打工者神情落寞地坐在老厉对面,原来他被单位无故解除劳动关系,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
老厉听出了对方心中的怨气,马上引导他通过仲裁方式寻求法律上的经济补偿。
“一个人对人民的服务,不一定要站在大会上讲演或是作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随时随地,点点滴滴地把自己知道的、想到的告诉大家,无形中就是替国家播种、垦植。
”老厉非常喜欢傅雷的这段话。
像厉民一这样的老干部很多,他们退休后,有的自发的在社区为老百姓服务,有的协助法院做好诉前调解,有的帮忙监察室做好审务督查工作,还有的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以讲课形式与更多年轻人分享。
“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老干部处的工作就是做好服务与保障,发挥老同志们的特长,让他们更好地为社会增添正能量。
”丁美玲说,也正因为此,她要求团队的人在保障老干部及家属权益方面不能有一点闪失。
离休干部老王生前留有一笔数额不小的存款,熟悉老王家庭情况的张为人处理老王后事时特别谨慎,他知道老王曾经领养过一个女儿,后来养女与后母关系不佳,一气之下离家而走。
“从法律上讲,养女也有继承权利的,她不签字,我这里无法发抚恤金。
”张为人委婉地向老王后妻解释法律规定。
“已经多年没有联系她了,怎么办?”王妻问道。
看到王妻有所松动,张为人赶紧翻开档案找到养女的联系电话,然后给了王妻。
接到后母电话的养女连忙赶到老王 上海高院老干部处集体合影,左起依次为贾蕾、赵红、田苏香、丁美玲、刘永深、张为人、张锐。
孟招祥摄 的遗体告别仪式现场,想起养父曾经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养女深感内疚,与后母也冰释前嫌。
到法院领取抚恤金当天,养女和后母在法院拍了张合影,养女轻轻对后母说:“阿姨,以后我们要多来往来往。
” 遗愿清单 在老干部处工作的人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那是其他部门所不会遇见的,那就是——面对死亡。
“有时候家属突然打电话来说,人已经到最后了,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过去,能见最后一面就见,不能见最后一面,也要去家中慰问,问一问家属有什么需求。
”刘永深说。
抚恤金如何发放、讣告生平内容怎么写,甚至花圈怎么摆放、挽联顺序如何,一切都是细节活儿。
然而,这还不是最揪心的,最难做的是面临死亡时如何劝慰患病的老同志。
很多人都是大限将至时,才第一次认真思考死亡。
张伟永远也忘不了,在父亲生命最后的一年零八个月里,老干部处给予父亲和他的支持。
老张曾担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经济庭庭长、副院长,后调至上海高院担任经济庭庭长、审委会委员、副巡视员,然后退休。
在张伟的童年记忆里,父亲从早到晚地加班,有时候还是华政的指导老师,平日里只要弄堂里哪家发生纠纷,必然会找父亲来主持公道。
善良、敬业、坚强,这是父亲留给张伟的印象,他从未见过父亲流眼泪。
2013年,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张与妻子度过了金婚纪念日,不久,老张发现自己的声音变哑了,人也在渐渐消瘦。
张伟陪着父亲前往中山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张伟一个噩耗:“你父亲得的是运动元神经,俗称渐冻症,所有神经技能会一一丧失,最后呼吸衰竭而死。
这个病是不可逆的,无药可救。
”医生给张伟推荐了一个可以延缓病情发展的药。
张伟懵了,他强忍着悲痛和妹妹商量,最后决定暂时不告诉父亲病情,而是购买药物以延缓父亲病情的发展。
细心的他给药物的包装和说明书做了“手脚”,避免父亲得知真相。
然而,老张还是发现了。
一次,他无意间听到医生在走廊上的对话,医生说他的病实际就是“死刑缓刑”。
老张大怒,一下子吵到了医务处,医患矛盾骤升,医院只得打电话找到了老干部处。
丁美玲很理解老张的心情,在老张之前,已经有一位老干部因为相同的病症而去世。
听着老张喋喋不休的“控诉”,丁美玲知道自己说什么劝慰的话都是无用的。
她“扳”起了脸“:老张,医生在走道上随意议论病人病情是不对,但他说的是实情。
一个人的生命长度是老天定的,但生命的宽度则是自己定的,开开心心是一天,焦虑不安也是一天,老张,希望你加大宽度,快乐过好每一天。
” 丁美玲的“当头一棒”喝醒了老张。
过了一段时间,丁美玲再去看望老张,老张拿着台历上自己写的字给她看:“无论碰到什么困难,我希望不屈不挠,让每天都充满希望和愉快,与患难为友,绝望也能锻炼我,摆正长度与宽度的关系,过好每一天。
” 2014年5月,老张因脚肿住进医院,此时的他伴有强烈的咳嗽却无法咳出痰液。
一个星期后,生命体征降到最低,医院开出病危通知书,并询问家属是否需要切开气管。
切还是不切?张伟陷入痛苦之中。
不切,父亲有可能会失去生命;切开,以后的生活质量就一落千丈。
最后,张伟签字同意切开气管。
抢救回来的老张躺在ICU里,张伟通过写字板和父亲交流,老张在纸上慢慢写:“我还想要活下去,你帮我多活两年。
”张伟强忍泪水写到:“你放心,时间长着呢。
” 然而,情况总是超乎家人的想象,老张的心脏不断出现异常,病危通知书一张接着一张,每次丁美玲都会及时赶来,张伟后来才知道,当时丁美玲的父亲也在重病住院。
老张的脾气越来越焦躁,一次,他吵着要搬出ICU,一怒之下把写字板扔在张伟身上,张伟低头一看纸条,上面写着:“我再也不相信医院了!” 无奈的张伟只得打电话叫来丁美玲。
当丁美玲一走进ICU时,老张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不能哭,你再哭我就走了。
”丁美玲一边说一边打手势,“把眼泪忍住,不哭了。
你不能激动,你一激动心脏病要加重,放松,笑一笑!” 老张听话地抿紧嘴唇,强忍眼泪,又点头又摇头。
从没见过父亲哭过的张伟心酸不已,这就是曾经坚不可摧的父亲啊! “第
一,你要配合治疗,你想换病房,大家都理解,目前没有条件,我们正在争取。
再等两天,你相信我吗?”丁美玲问。
老张使劲儿点头,情绪一下子平静下来。
一年零八个月,这是老张人生中难熬的一段岁月,也是老张家人悲伤心碎的一段日子。
“回去问你妈妈好,让她照顾好自己,这里有我们。
”丁美玲不止一次地提醒张伟。
最后的日子里,老张常常眼神定定地望着天花板,一望就是一两个小时,张伟和他说话,他也没有反应。
只有当丁美玲来病房看望他时,老张的嘴角才会努力上扬一下,有时候是嘴唇抿一下。
2016年1月6日,老张于凌晨5时离开人世,离世前,张伟在父亲的耳边轻轻说:“爸爸,你安安心心走吧,我每年会来看你的。
你有什么告诉我,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 1月8日,丁美玲参加完老张的遗体告别仪式,错过了前往重症监护室探望自己父亲的时间,第二天,老父亲去世。
“父亲这里,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虽然我没有看到他最后一眼。
”丁美玲说,“我现在对人生看得比较透,人的生命很珍贵,但是要有尊严,有尊严地活着,有尊严地走。
” 2016年12月23日,上海高院老干部处被授予“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这是一次各行各业老干部工作的评比,是上海法院前所未有的殊荣,“高老微”微信群兴奋不已,大家交口称赞老干部处“当之无愧”。
丁美玲作为先进集体代表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表彰大会。
2016年8月,丁美玲升为上海高院副巡视员,再过1年,她也即将退休。
2017年3月,老干部处的田苏香退休,开始回家带孙子。
2017年1月,39岁的王薇加入老干部处,成为处里的又一位新人。
“在法院工作的人,一生中待得最久的部门就是老干部处,退休以后都归老干部处。
”丁美玲的话萦绕在记者的耳旁。
责任编辑陈冰新闻热线(010)67550710电子信箱chenbing@ 欢迎广大读者提供人物报道稿件或线索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