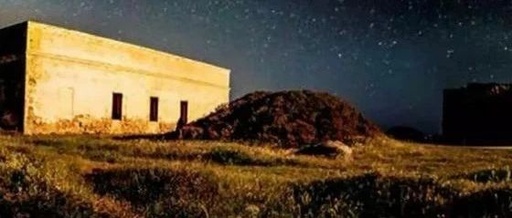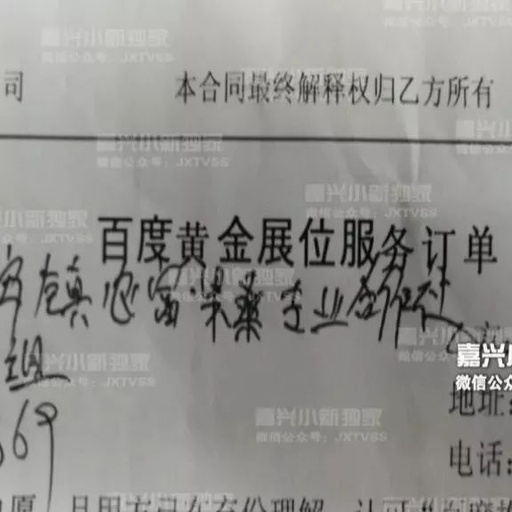10版月光城
2020年12月25日星期五责编魏振强E—mail:oldbrook@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捕头
肖遥
前几天跟朋友小萌聊天,说着说着她就会看一下手机,看见我投来诧异的小眼神,她抱歉道:“不好意思,我得处理一下工作。
”小萌刚接手内勤工作,她自谦自己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内勤,文件一来,她先火烧火燎手忙脚乱。
尤其是上周,本市食品抽检发现一例冷冻海鲜的盒子上有病毒,她就不得安生了,大周末的,好几个人加她微信,隔几分钟发一个指令,一会儿让报数据,一会儿让报总结。
小萌感慨,从前的机关内勤,最忙的时候是抱着文件一路小跑,仿佛有谁埋伏在路上准备袭击他们一样。
如今大数据时代的内勤,累的不是腿了,是眼睛。
只要你醒着,就得抱着手机守着电脑,每过5分钟刷一下屏,等着各部门的文件流转过来。
从前可以甩锅给纪要或者给其它部门:纪要的电话没接到,其它部门没说清。
只要对方是人而不是机器,就有可能犯错。
可如今每个部门都能看到手机软件上的文件,纪要没义务通知内勤了。
内勤必须分分钟留意着,才能不错过新文件。
像打球一样,这边一发球,那边就得成功接住。
于是,内勤们的职能就像专们捕捉文件的捕头,把弹出的一个新文件打开,就像捉住一只鸟,内心还有些小激动。
众目睽睽之下,没看见新文件跳出来的内勤,就像没逮住猎物的猎人一样失职。
这个游戏刚开始玩会很乏味,时间长了就被训练得眼疾手快,再往后小萌发现自己已经被游戏规则绑架——上厕所前一秒还要刷新一下电脑,看有没有蹦出新文件。
小萌已经把自己训练得像狙击手一样,文件一冒头就击毙。
最好一枪命中,文件存活时间越长,自己作为专业的狙击手就越失败。
内勤对文件变得又爱又恨,半天没有新文件,还会隐隐失落。
一有新文件,就会进入备战状态,全力以赴歼灭它,有一种上战场杀敌的快感。
小萌说从前做外勤,处理案件的时候,最烦这些内勤。
私底下叫他们“表哥表姐”,觉得表哥表姐们啥业务能力也没有,就会催数据填报表。
直到自己也做了内勤,也变成催命鬼,才明白内勤的工作动力不在于权力欲,在于撇清自己,一个报表按时报了,自己的责任就撇清了,板子就打不到自己身上了。
就像小时候玩的“打沙包”的游戏,看谁闪转腾挪得快,看谁不被呼啸而来的沙包打到。
《摩登世界》里流水线上的工人的心态应该如此,只有把接收文件统计数据当做一种机械的工作,这项工作才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成为一种下意识的动作。
这动作无论再无聊、乏味、画蛇添足,但因为每天都做,做得久了,竟然习惯成自然,成了必选动作。
何况,因为有了一大坨人的参与,变成了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就像小时候吃饭磨磨蹭蹭,大人就会说“快吃,看看那个谁来了,来比比看谁吃的快!”小孩子会下意识地加快速度,也不论味道了,也不管有没有食欲了,忘了手里正玩的玩具和嘴里正聊的话题,赶紧往嘴里扒拉饭,生怕被“那个谁”比下去了。
跟从前的一线工作比,小萌现在算是后台了,除了和数据、软件和文件较劲,不用处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了。
可她总怀念从前办案子的日子,虽然那时天天面对的是动辄跟你吹胡子瞪眼,把你当对手当敌人的陌生人,可也比变成采集数据的机器人强。
大地经络许萍摄 桕籽树 李凤仙 树活到一定岁数时,很多会成为地标。
在房屋、道路格局大同小异的乡村,往往搞不清走哪条路,问荷锄的、挎菜篮的,他们都会用老树枝一样的手,指着某条路,说,看到了那棵大枫树吗?走到那里就到了。
刚到这所“老山里”的小学工作,路盲的我,经一只老树枝一样的手指路后,就记住了那棵桕籽树。
每次远远看到它侯在路口,心里就暖乎乎的,仿佛久别回家,我的父母看我一步一步走进家门。
老桕籽树送走了长长的秋天,冬天撵着秋天的尾巴来了。
山里的冬天不那么冷硬、尖刻,有点倒春寒的柔韧。
如果是细雨霏霏的天,灰白的玉带一样的雨雾锁在山腰,山顶仙云翻覆,山脚泼碧淌翠,细雨迷离中的山村就像是一幅水墨画,而老桕籽树就是闲笔。
老桕籽树斜斜地倚在人家的脚屋檐上,像累了的老农倚着一棵大树,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在袅袅的青烟里若隐若现。
桕籽树太老了,爆裂的皮像破碎的龟壳。
它们身上的苔藓,嫩绿得像刚拱出土的春草,把树干当成假山攀爬,薄毡般紧贴树干,给老桕籽树穿上了一件翠亮的衣裳。
桕籽树的枝干虬劲,没了叶子,在寒风里更显庄严、肃穆。
风拂得田沟里萎黄的茭白沙沙如万蚕吃桑叶,但老桕籽树的枝石化了一样,不动声色。
桕籽树有多大年纪呢?问村里八十老翁,说不知道它多大,说他爷爷爬上去捋过桕籽,爷爷的爷爷也捋过。
桕籽树上有多少代人的手纹足印?现在没谁说得上来。
老桕籽树是幸运的。
它曾经遭过火灾,而且还是天火。
一个久旱的冬天,靠它堆就的一个柴堆着火了,冲天的火光,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惊醒了沉睡的村民。
大家冲出家门,张家桶李家盆,在火光里穿梭,人们呼喊着,奔跑着,一桶桶水,一盆盆水泼向舔着天空的火焰。
眼看火势弱下来了,突然啸起一阵狂风,火苗呼地一下蹿上了正房,稻草屋顶瞬间成了火海。
桕籽树叶烧得像火山喷熔岩。
老人哭天抢地,小孩哇哇乱叫,狗惊恐狂吠……猛然间,一道闪电把天空撕开了几道血口,“轰!轰”,“哗……”,暴雨如注…… 火灭了。
桕籽树侥幸活了下来,它斜靠着人家的脚屋,屋子修缮过好几次,但谁也没有砍去桕籽树的一根枝桠。
村里人都说桕籽树大难不死,一定是神灵相救,说神灵只救好人,那么这棵树一定是好树。
说一个村子里有好树,村里人一定会活得像那棵树。
桕籽树站在路边。
路还是窄得只容一头牛独行的泥巴路时,它就站在路边。
泥巴路拓成石子路时,谁也没伤它一片叶子。
石子路铺成水泥路时,对面人家的晒床更小了,但桕籽树的领地还是那么大。
弱者的反击 冯磊 读到过一则朱安女士的往事。
在八道湾居住期间,周家为鲁瑞过寿。
因为鲁迅兄弟的影响力,前来参加宴会的宾客自然不少。
开席之前,朱安女士穿戴整齐,缓缓地从房中走了出来。
之后,“扑通”一声跪在众人面前。
说道:“我来周家已经许多年了,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
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
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
”说完,叩头离开。
读了这段文字,感觉震惊。
在我的印象中,朱安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她就像一个影子,偶尔从各类文字的丛林中探出头来。
这些文字,有些是近年来整理的八卦资料。
还有一些,见诸于当年的报刊。
在《鲁迅全集》中,朱安这个陪伴鲁迅几十年的女子,从未露过面。
有时提及她,大先生那浓黑的笔端也只用一个“妇”来替代。
一个“妇”字,就道尽了她的一生。
这一生可谓憋屈。
她熟悉《女儿经》,知道温良恭俭让那一套旧式规矩。
每个早晨,她都恭恭敬敬地向婆婆鲁瑞请安。
在丈夫面前,她大气都不敢出。
她挖空心思烹调出可口的饭菜,希望通过俘虏丈夫的胃来俘获丈夫的心。
但是,那个在母亲面前温顺如绵羊的男子,在她面前就是一座倔强的冰山。
……她没有孩子。
虽然,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鲁瑞曾奇怪地问她,为什么不要一个孩子(很多人认为,这是拴住男人的一个办法。
实际上,有时也颇有用)?她幽幽地说,大先生不与我说话。
数十年来,朱安就像一件家具,被摆在周家的客厅里。
然而问题在于,她不是一件家具。
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她有感情,有寄托,有思想,有欲望。
她烧菜的手艺很好,她对丈夫死心塌地,她愿意跟随他走南闯北,她卑微渺小不求回报……但是,这种种好处都被人忘却和忽略了。
她走得越来越远,以至于最终浓缩为一个小小的“妇”字。
当世人将目光投向那个大声疾呼“救救孩子”的人,投向那个用一腔热血拯救民族精神的长者的时候,谁曾料到:那巨人的阴影里,无情掩埋了一个矮小而瘦弱的身躯!毫无疑问,朱安是温婉的,也是倔强的和绝望的。
绝望,伴随了她的后半生。
这种绝望,根源于鲁迅对她的态度上,也源于周家大部分人,以及公众对她的态度上。
她是一个多余的人!在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当所有人都忙着把温情和关怀投向那些“进步”的人士,却完全忽略了一个弱者的感受。
她从绍兴来,裹着小脚。
多少年来,她一直试着用自己的贤良,挽回那颗激进的心。
结局,是一败涂地。
这个万分沮丧的女子,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来了惊天一跪,试图用舆论改变自己惨淡的宿命。
却不料,竟将其越推越远。
——不久之后,当鲁迅弃她而去,她才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
朱安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
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
”不要埋怨弱者的心机。
哪怕,这微弱的反抗在外人看来是如此的无助和可笑。
在春天和夏天成长起来的人儿啊,要学会理解冰天雪地中那些弱者的艰辛。
他们或者她们,犹如大潮中的一叶扁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他们最需要的,恰恰是他人的理解和包容。
哪怕是,从阴暗墙角里传递过来的一丝暖意。
”小萌刚接手内勤工作,她自谦自己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内勤,文件一来,她先火烧火燎手忙脚乱。
尤其是上周,本市食品抽检发现一例冷冻海鲜的盒子上有病毒,她就不得安生了,大周末的,好几个人加她微信,隔几分钟发一个指令,一会儿让报数据,一会儿让报总结。
小萌感慨,从前的机关内勤,最忙的时候是抱着文件一路小跑,仿佛有谁埋伏在路上准备袭击他们一样。
如今大数据时代的内勤,累的不是腿了,是眼睛。
只要你醒着,就得抱着手机守着电脑,每过5分钟刷一下屏,等着各部门的文件流转过来。
从前可以甩锅给纪要或者给其它部门:纪要的电话没接到,其它部门没说清。
只要对方是人而不是机器,就有可能犯错。
可如今每个部门都能看到手机软件上的文件,纪要没义务通知内勤了。
内勤必须分分钟留意着,才能不错过新文件。
像打球一样,这边一发球,那边就得成功接住。
于是,内勤们的职能就像专们捕捉文件的捕头,把弹出的一个新文件打开,就像捉住一只鸟,内心还有些小激动。
众目睽睽之下,没看见新文件跳出来的内勤,就像没逮住猎物的猎人一样失职。
这个游戏刚开始玩会很乏味,时间长了就被训练得眼疾手快,再往后小萌发现自己已经被游戏规则绑架——上厕所前一秒还要刷新一下电脑,看有没有蹦出新文件。
小萌已经把自己训练得像狙击手一样,文件一冒头就击毙。
最好一枪命中,文件存活时间越长,自己作为专业的狙击手就越失败。
内勤对文件变得又爱又恨,半天没有新文件,还会隐隐失落。
一有新文件,就会进入备战状态,全力以赴歼灭它,有一种上战场杀敌的快感。
小萌说从前做外勤,处理案件的时候,最烦这些内勤。
私底下叫他们“表哥表姐”,觉得表哥表姐们啥业务能力也没有,就会催数据填报表。
直到自己也做了内勤,也变成催命鬼,才明白内勤的工作动力不在于权力欲,在于撇清自己,一个报表按时报了,自己的责任就撇清了,板子就打不到自己身上了。
就像小时候玩的“打沙包”的游戏,看谁闪转腾挪得快,看谁不被呼啸而来的沙包打到。
《摩登世界》里流水线上的工人的心态应该如此,只有把接收文件统计数据当做一种机械的工作,这项工作才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成为一种下意识的动作。
这动作无论再无聊、乏味、画蛇添足,但因为每天都做,做得久了,竟然习惯成自然,成了必选动作。
何况,因为有了一大坨人的参与,变成了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就像小时候吃饭磨磨蹭蹭,大人就会说“快吃,看看那个谁来了,来比比看谁吃的快!”小孩子会下意识地加快速度,也不论味道了,也不管有没有食欲了,忘了手里正玩的玩具和嘴里正聊的话题,赶紧往嘴里扒拉饭,生怕被“那个谁”比下去了。
跟从前的一线工作比,小萌现在算是后台了,除了和数据、软件和文件较劲,不用处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了。
可她总怀念从前办案子的日子,虽然那时天天面对的是动辄跟你吹胡子瞪眼,把你当对手当敌人的陌生人,可也比变成采集数据的机器人强。
大地经络许萍摄 桕籽树 李凤仙 树活到一定岁数时,很多会成为地标。
在房屋、道路格局大同小异的乡村,往往搞不清走哪条路,问荷锄的、挎菜篮的,他们都会用老树枝一样的手,指着某条路,说,看到了那棵大枫树吗?走到那里就到了。
刚到这所“老山里”的小学工作,路盲的我,经一只老树枝一样的手指路后,就记住了那棵桕籽树。
每次远远看到它侯在路口,心里就暖乎乎的,仿佛久别回家,我的父母看我一步一步走进家门。
老桕籽树送走了长长的秋天,冬天撵着秋天的尾巴来了。
山里的冬天不那么冷硬、尖刻,有点倒春寒的柔韧。
如果是细雨霏霏的天,灰白的玉带一样的雨雾锁在山腰,山顶仙云翻覆,山脚泼碧淌翠,细雨迷离中的山村就像是一幅水墨画,而老桕籽树就是闲笔。
老桕籽树斜斜地倚在人家的脚屋檐上,像累了的老农倚着一棵大树,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在袅袅的青烟里若隐若现。
桕籽树太老了,爆裂的皮像破碎的龟壳。
它们身上的苔藓,嫩绿得像刚拱出土的春草,把树干当成假山攀爬,薄毡般紧贴树干,给老桕籽树穿上了一件翠亮的衣裳。
桕籽树的枝干虬劲,没了叶子,在寒风里更显庄严、肃穆。
风拂得田沟里萎黄的茭白沙沙如万蚕吃桑叶,但老桕籽树的枝石化了一样,不动声色。
桕籽树有多大年纪呢?问村里八十老翁,说不知道它多大,说他爷爷爬上去捋过桕籽,爷爷的爷爷也捋过。
桕籽树上有多少代人的手纹足印?现在没谁说得上来。
老桕籽树是幸运的。
它曾经遭过火灾,而且还是天火。
一个久旱的冬天,靠它堆就的一个柴堆着火了,冲天的火光,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惊醒了沉睡的村民。
大家冲出家门,张家桶李家盆,在火光里穿梭,人们呼喊着,奔跑着,一桶桶水,一盆盆水泼向舔着天空的火焰。
眼看火势弱下来了,突然啸起一阵狂风,火苗呼地一下蹿上了正房,稻草屋顶瞬间成了火海。
桕籽树叶烧得像火山喷熔岩。
老人哭天抢地,小孩哇哇乱叫,狗惊恐狂吠……猛然间,一道闪电把天空撕开了几道血口,“轰!轰”,“哗……”,暴雨如注…… 火灭了。
桕籽树侥幸活了下来,它斜靠着人家的脚屋,屋子修缮过好几次,但谁也没有砍去桕籽树的一根枝桠。
村里人都说桕籽树大难不死,一定是神灵相救,说神灵只救好人,那么这棵树一定是好树。
说一个村子里有好树,村里人一定会活得像那棵树。
桕籽树站在路边。
路还是窄得只容一头牛独行的泥巴路时,它就站在路边。
泥巴路拓成石子路时,谁也没伤它一片叶子。
石子路铺成水泥路时,对面人家的晒床更小了,但桕籽树的领地还是那么大。
弱者的反击 冯磊 读到过一则朱安女士的往事。
在八道湾居住期间,周家为鲁瑞过寿。
因为鲁迅兄弟的影响力,前来参加宴会的宾客自然不少。
开席之前,朱安女士穿戴整齐,缓缓地从房中走了出来。
之后,“扑通”一声跪在众人面前。
说道:“我来周家已经许多年了,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
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
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
”说完,叩头离开。
读了这段文字,感觉震惊。
在我的印象中,朱安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她就像一个影子,偶尔从各类文字的丛林中探出头来。
这些文字,有些是近年来整理的八卦资料。
还有一些,见诸于当年的报刊。
在《鲁迅全集》中,朱安这个陪伴鲁迅几十年的女子,从未露过面。
有时提及她,大先生那浓黑的笔端也只用一个“妇”来替代。
一个“妇”字,就道尽了她的一生。
这一生可谓憋屈。
她熟悉《女儿经》,知道温良恭俭让那一套旧式规矩。
每个早晨,她都恭恭敬敬地向婆婆鲁瑞请安。
在丈夫面前,她大气都不敢出。
她挖空心思烹调出可口的饭菜,希望通过俘虏丈夫的胃来俘获丈夫的心。
但是,那个在母亲面前温顺如绵羊的男子,在她面前就是一座倔强的冰山。
……她没有孩子。
虽然,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鲁瑞曾奇怪地问她,为什么不要一个孩子(很多人认为,这是拴住男人的一个办法。
实际上,有时也颇有用)?她幽幽地说,大先生不与我说话。
数十年来,朱安就像一件家具,被摆在周家的客厅里。
然而问题在于,她不是一件家具。
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她有感情,有寄托,有思想,有欲望。
她烧菜的手艺很好,她对丈夫死心塌地,她愿意跟随他走南闯北,她卑微渺小不求回报……但是,这种种好处都被人忘却和忽略了。
她走得越来越远,以至于最终浓缩为一个小小的“妇”字。
当世人将目光投向那个大声疾呼“救救孩子”的人,投向那个用一腔热血拯救民族精神的长者的时候,谁曾料到:那巨人的阴影里,无情掩埋了一个矮小而瘦弱的身躯!毫无疑问,朱安是温婉的,也是倔强的和绝望的。
绝望,伴随了她的后半生。
这种绝望,根源于鲁迅对她的态度上,也源于周家大部分人,以及公众对她的态度上。
她是一个多余的人!在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当所有人都忙着把温情和关怀投向那些“进步”的人士,却完全忽略了一个弱者的感受。
她从绍兴来,裹着小脚。
多少年来,她一直试着用自己的贤良,挽回那颗激进的心。
结局,是一败涂地。
这个万分沮丧的女子,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来了惊天一跪,试图用舆论改变自己惨淡的宿命。
却不料,竟将其越推越远。
——不久之后,当鲁迅弃她而去,她才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
朱安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
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
”不要埋怨弱者的心机。
哪怕,这微弱的反抗在外人看来是如此的无助和可笑。
在春天和夏天成长起来的人儿啊,要学会理解冰天雪地中那些弱者的艰辛。
他们或者她们,犹如大潮中的一叶扁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他们最需要的,恰恰是他人的理解和包容。
哪怕是,从阴暗墙角里传递过来的一丝暖意。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